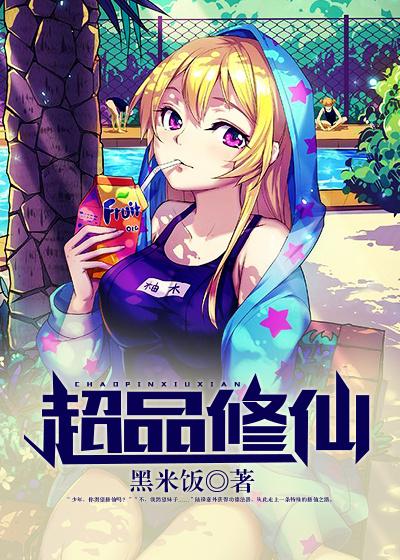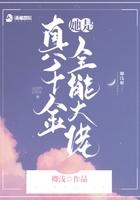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给捉妖师一颗心 > 歹人行凶(第1页)
歹人行凶(第1页)
山村几乎与世隔绝,附近没有大的城镇,因着歧路难行,村民们一年到头也鲜少出去,偶有商贩来此,与之换些简易小物,旁的他们也买不起。
勤快些的人种几块地便能得活,亦或者承袭祖辈传统,种植草药去卖钱;而那懒惰之人,要么靠着祖上的微薄积蓄穷苦度日,要么碘着脸去屯粮储借米,以保他们果腹。
这是建村以来留下的传统,家中收成好的人家需得交一箩粮到屯粮储,一来可保灾年不受饿,二来也给收成不好的人家留个活路。借粮后,可明年用同等的粮食偿还,亦或者折算成现银相抵。
建村伊始,大家都以采药为生,方圆百里皆人迹罕至,且气候适宜,土壤丰沃,是颇适合植物生长的。祖先们将识药辨药的本事代代相传,后人也多是采药人,待到一年或半载,便组织人长途跋涉将药材运出去卖掉,再带回日常所需之物。
然而,人多药少,在这场供需不平衡的战争中,草药落败,它们大部分都绝迹,采药人也逐渐吃不上饭了。脑子活络些的,拖家带口离村,翻越崇山峻岭去外面寻个渺茫的发展机会,但大部分人还是留了下来。
为了解决困境,一些人开始想办法,既然野生的长不出来了,何不如自己种呢?
于是,村民们开始尝试自己种植草药,奈何他们毫无经验,大多以失败告终,但也有例外的,比如芍秧。
她是村里屈指可数的种药人,也乐意帮助村民,常能看见她躬身田地间,细心照料着一株株宝贝。
种药这条路走不通后,开始寻其他路径,有人重事农桑,有人进山打猎,当然也有游手好闲之辈。
锄地辛苦,每年上交的粮也减少,更何况还不上的,如今几乎是借不出了。
……
静谧的午间,芍秧刚为邻人传授完种植经验,走到树荫底下准备歇口气,耳边传来唤她名字的声音,探头去瞧了个清楚。
正是酽白三人。
芍秧一早出了门,忙到午时也不见回来吃饭,他们借助在人家家里,不收银钱已极为过意不去,总要做点什么聊表谢意。
常鹊羽酒劲儿过去,下厨炒了两个菜,忙提溜着给人送过来,揭开盖子,冒着热气儿的饭菜看着馋人,胃口一下上来了。
“真是麻烦你们,其实不用的,我带了饼子,总能对付两口。”许是经年累月的劳作,她吃惯了粗糙口粮,能饱腹便可。
芍秧接过碗筷在一旁吃着,与常鹊羽闲话家常,柳殷照无聊,待在酽白身旁发呆。
春末夏初的天气不冷不热,正是赏玩的好时节,可惜他们被耽搁在这里,不免幽幽叹气。
此处是小丘,从上往下看,一片郁郁葱葱,杂草和新生的树木长势疯狂,争先恐后的向上拔高,将黄土地遮掩得严严实实,那些可怜的低矮药草,逐渐被围杀在底部,始终不见主人来救它们。
等到芍秧将最后的活儿干完,几人一齐回家去,芍秧的地在村子最外边,每次来都要走很远,但她仍旧不辞辛苦,日日往返。
“芍秧,那边的地怎么秃了?”
目之所及是一连片的干涸黄土,泥块儿板结僵硬,不见丁点儿水分留存,其上也不如别地长满植物,哪怕是野草都不见几颗。
“之前种太多草药,现在地里没了肥,已经荒了好久。”
荒掉的地无人打理,一年更不如一年,它已经不能带来村民想要的东西了,理所当然的被抛弃。
越往回走越能瞧见人迹,连婶子正低头锄地,晃眼瞧见芍秧一行人,大声开口叫住他们,扔下手里的锄头从田埂那头跑过来。
“芍秧啊,正想着去找你呢。”
“你群叔那个老东西又骗你药材了吧,唉,我真是没脸见人了,拿他没办法啊,骂也骂不听,就改不了这个坏毛病。”
“好孩子,你下次可别再听他的,他说什么你都别管,就说是我叮嘱的,谁也别帮他,我有手有脚,啥不能干啊,非要去骗去偷……你记住婶子的话啊,下次别给了。”
正说着,前面坝子上传来一群小孩撕心裂肺的哭声,震得人耳朵痛。
一个黝黑汉子叉腰睨着小孩儿,嘴巴张张合合说着什么,几个孩子手里的白面馍馍被他一把夺过,三两口塞进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