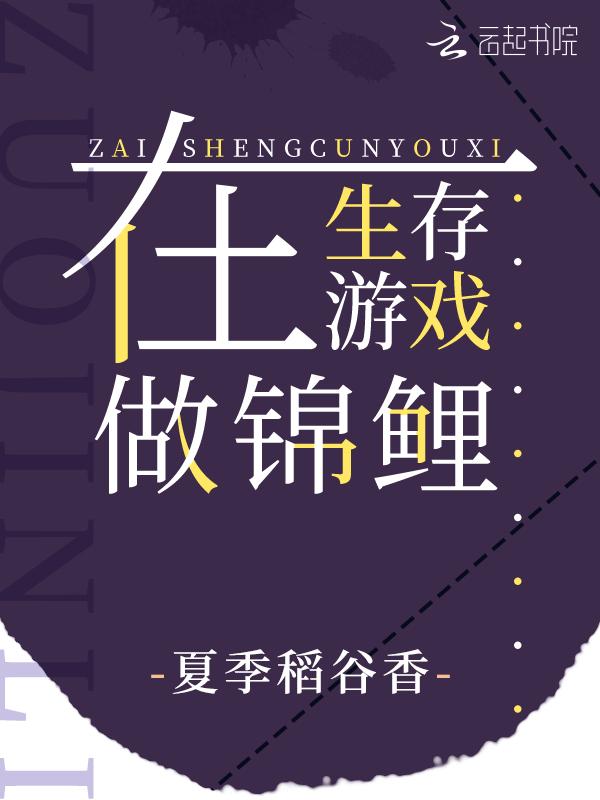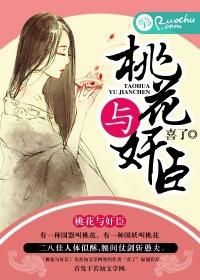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跟亡夫长兄借子后 > 3035(第23页)
3035(第23页)
田岁禾说:“那是因为你聪明,家人都巴望着你当大官儿。我就不一样了,阿翁不希望我认字,我也不是认字的料,别处也笨,所以从来不想跟人攀比,因为,”她耸耸肩,“比也比不过,干脆放了自己。”
宋持砚说:“这很好。”
好像聊到了他更不喜欢的话题了,田岁禾甚至感觉得到他周身的氛围又压抑了些,她决定放弃闲聊,突然拉住他的手,“阿砚,你牵牵我吧,我看别家夫妻出门都那样。”
宋持砚习惯性地抽出,改为握住她手腕。
他牵腕子的动作也不娴熟,田岁禾忍不住了,“谁家夫君牵娘子的手是握手腕啊,牵牛么?”
宋持砚问她:“那如何牵?”
她握住他的手,纤细的手指缓缓嵌入他的指缝,同样地,他粗大的手也徐徐欺入她狭窄的指缝间,十指相扣虽不如交吻亲昵,却暧昧仿若一场在大庭广众之下隐密进行的相互入侵。
宋持砚清冷的唇角抿了抿,收紧了与她契合的手。
田岁禾确保他不会突然跑掉,这才开始修补隔夜馍,“阿郎,你是不是变不回之前的阿郎了。”
宋持砚的手一紧,声音有些距离感:“你很想我变成阿郎?”
田岁禾反问:“你想么?”
宋持砚停下前行,扭过头深邃的目光看了她一会,冷淡而坚决地吐出两个字。
“不想。”
他等着她或是失望,或是恼怒,或是不解的反应,田岁禾仰头望着湛蓝的天,好久之后耸耸肩膀,重重地呼出一口气。
宋持砚退了半步:“但我会尽力待你好,不会因为不是阿郎而亏待你。”
田岁禾转过脸,竟是笑靥如花,洁白莹润的牙在阳光下宛若白玉。“没关系,你不想再做阿郎,那我就去习惯现在的你,好不好?”
她像在哄他。
宋持砚匪夷所思地皱眉,“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很快又说:“你不必为了我违背本心。”
就像他也不会为了她而迫使自己成为阿郎,他只会试图取而代之,男女情事跟官场之事不都一样么?皆是由人心引发的对弈,谁技高一筹,谁就能做占有的一方。
“我不是在违背。”田岁禾捧起他们交握的手,脸在他的手背上亲昵地贴贴,“我是觉得,以前的你有以前的好,现在也有现在的好,既然你不愿变回以前,我也挺喜欢现在的你。”
宋持砚眉头皱得更紧了。
“好在哪里?”
田岁禾认真细数:“你现在变白了,长高了,更好看了。有了学识,办事更冷静了,让我觉得很踏实,还有……亲亲的时候也很……哎,在外头说这些,怪羞人的。总归好的地方多着呢,你不用非要变回去的。”
宋持砚听完一句话也没有,只是紧紧盯着她,田岁禾被他盯得愣住,周围人来人往,但他们就像一对亘古的石像。
被盯了太久,田岁禾不满。“你不要太当自己是一回事,我会想念之前的你,还不是因为现在你虽然好,可总让我去猜,故意吊着我、捉弄我,还有!就像现在,经常莫名奇妙盯着我,看得我后背发凉……”
她数落着,发觉他还是在盯,田岁禾不高兴了。“喂!说你呢……哎!”
宋持砚忽然牵着她往一旁的巷子里走,什么也不说,虽然有在迁就她走得不算快。他突然这样,田岁禾一头雾水。
“带我来这干嘛?”
宋持砚什么话也没说,把她压在墙上,低下头继续盯着她。
目光好像能灼烧人,田岁禾双手摸了一把自己的脸,手上没有东西啊。不大确信,她又摸了摸,像猫儿在用一双爪子洗脸。
“没东西啊……”
她不解地眨着眼看宋持砚,他盯着她的眼神越发深沉了,她想起某些曾在黑暗中隐晦而温和的侵略,面上浮起潮红,噙着暧昧春意。
宋持砚撬开她的唇瓣,舌头长驱直入。
田岁禾身躯一震。
这、这……舌头第一次被他缠住,怎么会是这样奇怪的感觉?她的触感都从舌尖开始被他吸走,脑子昏得要命,人也好像要变成风筝飞上天。
好要命!她很害怕,不争气地咬了他。
宋持砚停下来,没有继续的打算,但依旧把她抵在了墙面与他臂弯合拢成的一片天地之间。
他用手指拂去她唇角被他留下的湿润,笑了一声。
很短暂的笑,似一只飞鸟迅速掠过湖面,田岁禾心上颤动涟漪,觉得他是在笑她笨拙,湿漉漉的眸子一翻,含羞带恼地道:“笑……笑什么,都是第一次,你也没熟练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