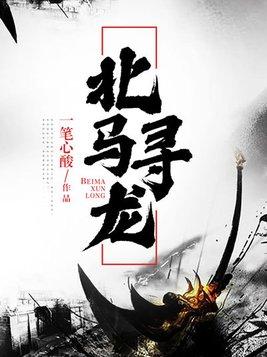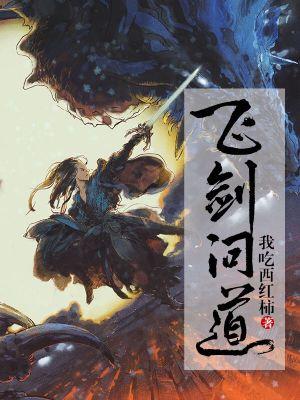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季汉上公,替关羽守荆州开始 > 第374章 四面皆围(第3页)
第374章 四面皆围(第3页)
他是陆舟,当年那个冒雨报信的少年,如今已是变律司首席顾问。他身后站着两名年轻人??一个是来自吕宋的混血少女,左眼失明,右眼嵌着水晶镜片,据说是波斯工匠为其特制;另一个是自幼失语的聋儿,却能在纸上写出比多数博士更精妙的算式。
“老师,您每年都来这儿站一整夜。”少女轻声问,“是在等什么吗?”
陆舟没有回头,只将伞微微倾斜,遮住那卷被风雨侵蚀多年的《薪火篇》复刻本。
“我在等一个回答。”他说,“当年那些孩子问‘海要变了’,我们给出了《动静图》。可如今,《动静图》也开始失效了。”
少女眉头微蹙:“您是说……天轴的倾斜速度加快了?”
“不止。”陆舟从怀中取出一封密函,纸面泛黄,盖着七枚不同地域的火漆印,“这是过去三个月内,从西域、漠北、南海、吐蕃、辽东、安南与昆仑山脚传来的联合观测记录。北极星移动速率翻倍,地磁紊乱导致罗盘失灵,连最老练的舵手也不敢出海超过三日。”
聋儿接过信笺,指尖轻轻抚过文字边缘,随即在随身携带的沙盘上写道:“难道……我们之前错了?不是天轴歪了,而是整个‘天穹’在滑动?”
陆舟缓缓点头:“有人提出,或许我们所在的‘天地’,本就是漂浮之物,如同海上的孤舟。若真是如此,那么所谓的‘星辰不动’,不过是错觉。”
少女倒吸一口冷气:“那岂不是说……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也在移动?”
“不错。”陆舟望向怒涛,“而且方向不明,速度未知。这才是真正的‘海要变了’??不是潮汐乱了,是我们所依存的世界,正在脱离旧有的轨道。”
三人陷入沉默。雨势渐歇,一道微弱的虹出现在东方天际,恰好横跨辰阳与远处海岛之间。
次日清晨,紧急钟声再度响起。
这一次,不是三长两短,而是连续九击??唯有“文明存续危机”方可启用的最高警讯。
七十二路灯首再度聚于桃李堂,墙上悬挂的《寰宇动静图》已被重新标注,红线如蛛网般交织,显示各地异常加速汇聚。林九渊虽已九十高龄,仍坚持站立发言。
“诸位,我们曾以为‘变’是挑战,如今才知,‘变’是常态。而人类唯一能做的,不是固守旧知,而是不断重建认知。”
会议决定重启“千童计划”,但此次不限于百人,而是面向全球招募“继光者”??凡愿投身真理探索者,不分年龄、国籍、身体状况,皆可申请加入新成立的“寰宇学社”。
首批响应者达万余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名年仅七岁的非洲女童,她从未受过正式教育,却能凭借沙画准确预测沙暴路径;还有一位瘫痪的罗马工程师,躺在担架上送来一份设计图??利用风力与地下水压差驱动的城市供能系统。
与此同时,辰阳开始建造“方舟书院”??一座可随海流缓慢移动的巨型平台,由百艘改造渔船连接而成,配备天文台、实验室、图书馆与农田。其核心理念源自沈螺晚年提出的“动态求知”理论:既然世界不停运动,求知之地也不应固定。
十年后,第一艘“知识方舟”启航,载着三百名学者驶向太平洋深处。他们带着《薪火篇》、星盘、地震音谱仪、改良版风车提水机,以及一本尚未完成的新典籍??《问天录》。
书中第一章写道:
>“古人仰观天文,以为天圆地方;
>后人测影推算,始知地动星移;
>今人察万象变迁,恍然觉悟:
>所谓宇宙,非静止之画,乃流动之诗。
>我们不必寻找永恒的答案,
>只需保持永恒的提问。”
又三十年,地球进入新一轮气候剧变期。大陆边缘陆续出现新的浅海,古老山脉露出海底岩层,而北极冰盖几乎完全消融。幸赖百年积累的知识网络,人类并未陷入混乱,反而在各地建立起适应性社区:高原城邦依靠地热与垂直农场维生;沙漠绿洲采用非洲寻水术与汉地坎儿井结合技术;海上浮城则借鉴?家船居智慧,形成自治联盟。
而“万人皆师,万物皆课”的理念,已成为全球共识。每一座村庄都设有“共学角”,每一名孩童入学第一课,便是讲述陆舟带回的那枚贝壳。
某年春分,新一代启明祭在浮动书院举行。主持仪式的是一位双目失明却感知敏锐的少女,她是当年琉球孩童的后代。她站在甲板中央,手中捧着一盏以海藻生物光培育的活体灯,轻声诵读:
>“心之所向,非庙堂之高,非金玉之贵;
>乃村塾一烛,童子一声,师者一笔。”
话音落下,百艘方舟同时点亮灯火,光芒连成一片,倒映在平静的海面上,宛若银河坠落人间。
而在遥远的太空观测站中,一组由中国与阿拉伯科学家联合发射的“观天镜”正缓缓旋转。它捕捉到一颗遥远行星的大气成分变化,显示出类似地球早期生命的信号。
控制室内,一名年轻研究员看着数据流,忽然笑了。他在日志中写下:
“也许有一天,那里也会有人捡起一块石头,用炭条写下:
**‘我们要学算术,因为海要变了。’**”
他抬头望向星空,轻声道:“到时候,我们也该送去一盏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