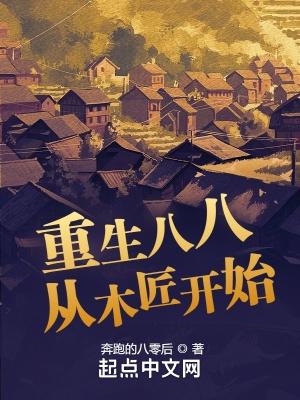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重生1977大时代方言朱琳笔趣阁最新列表 > 第1465章 廖主任的关心安排保镖(第2页)
第1465章 廖主任的关心安排保镖(第2页)
朱韵站在我身后,轻声说:“这不是一天写成的。
这些人……他们来过很多次。”
我点点头。
这种地方,如今在全球各地悄然出现??地铁隧道尽头、废弃教学楼黑板、深夜便利店留言板。
它们没有组织,没有号召,却自发形成了某种“提问圣地”
。
就像远古人类围着篝火讲述神话一样,现代人开始用问题构筑精神图腾。
我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在空白页写下一句新的话:
>“也许,真正的自由不是说出你想说的,而是问出你不敢问的。”
然后把它夹进墙缝,任风吹动纸页。
夜深时,我们在一间乡村旅馆落脚。
房间狭小,暖气片嘶嘶作响,窗外是一片结冰的湖面。
朱韵泡了杯速溶咖啡,靠在床上翻看手机??一台改装过的量子共振终端,能捕捉全球范围内高密度“疑问波动”
信号。
“你看这个。”
她递过屏幕。
地图上,数百个光点闪烁不息,主要集中在教育机构、医院儿科病房、监狱阅览室和老年社区中心。
最亮的一个,竟位于撒哈拉沙漠深处的一所游牧民族学校。
“那里只有一个老师,六个学生。”
她说,“但他们每周都会举行‘无答案日’,所有人必须提出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并轮流解释为何这个问题值得存在。”
我凝视着那颗孤星般的光点,忽然觉得眼眶发热。
“我们当初建立‘归墟’协议时,以为需要超级计算机、加密网络、时空锚点……”
我苦笑,“可现在看来,真正让它存活下来的,不过是人心中那一丝不肯熄灭的好奇。”
朱韵看着我,眼神温柔:“所以你从来不是唯一的变量。
你是第一个点燃火柴的人,但火焰之所以不灭,是因为有太多人愿意伸手接过。”
那一夜我没睡好。
梦里又回到了1977年的矿井。
黑暗浓稠如沥青,空气闷热得让人窒息。
我被困在塌方的巷道里,头顶压着千钧岩石,耳边只有滴水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搜救犬吠叫。
但我没有呼救。
我只是躺在那里,仰望着头顶裂缝中透进来的一线微光,心里反复问一个问题:
>“如果我的死亡能换来一次重来的机会,那这次重生的意义,是不是就是为了告诉别人??别怕问错?”
就在这个念头升起的瞬间,梦境崩解。
我猛地睁眼,窗外天色微明,冰湖表面浮现出一圈圈同心圆般的雾纹,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深处缓缓上升。
我披衣出门,踩着薄霜走到湖边,发现整片湖面竟开始融化,尽管气温仍在零下。
更诡异的是,融化的水中浮现出无数气泡,每个气泡破裂时,都会发出一个音节??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声调,拼凑起来竟是一句完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