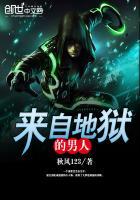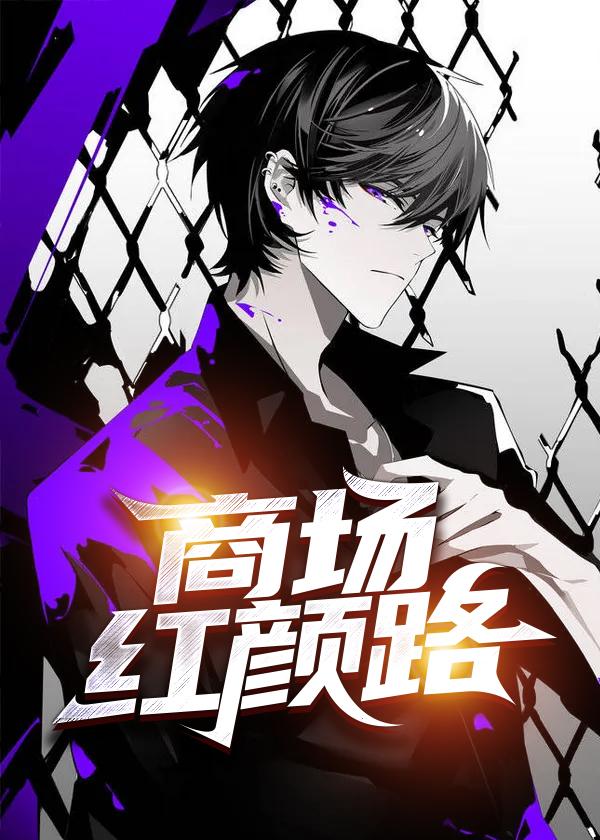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今天毁灭大宋了吗? > 第一百四十六章 要整顿野史朕可不想被传卖钩子石锤赵烁是穿越者(第3页)
第一百四十六章 要整顿野史朕可不想被传卖钩子石锤赵烁是穿越者(第3页)
她颤抖着翻到最后一页,只见空白处用钢笔写着:
>“本书由‘第九井编纂委员会’修订。版本号:Y-2025-01。献给所有不敢闭嘴的人。”
>
>落款日期是三天后。
教室陷入长久的寂静。
一个小男孩忽然举手:“老师,这些是真的吗?”
老师望着窗外纷飞的大雪,许久才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我知道,如果没人说,它们就会变成假的。”
春天来临时,全国档案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访问潮。一位四川老人查到了自己哥哥1952年被划为“反革命”处决的原始判决书,上面赫然写着:“证据不足,但需震慑群众,故判死刑。”
他在阅览室当场昏厥。
另一位上海女子找到了母亲1976年的日记复印件,其中一页写道:“今天女儿问我,为什么外公的名字不能提?我说,有些名字就像井里的水,越捂越臭。”
她在回家路上拨通了多年未联系的父亲的电话,第一句话是:“爸,我想听听爷爷的事。”
最令人震撼的是,在西北某军事基地旧址地下仓库,考古队发现了一个密封铁箱,内藏三千余封未寄出的信件。写信人全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监禁的知识分子,内容涵盖政治批判、家庭思念、科学构想、文学创作。每一封信的结尾,几乎都写着同一句话:
>“此信永不得寄出,唯愿后人知我曾思,曾痛,曾爱。”
这些信件经数字化处理后上传至“民间记忆共享数据库”,访问量瞬间突破千万。有人统计,平均每封信被阅读**2次**,相当于每个中国城市都有人在看。
而在沙洲的茶馆里,陈砚舟收到了一封没有寄件人的信。信纸是旧式的稿纸,墨迹微微晕染,像是用手写而非打印。
信中写道:
>“你一直在问‘谁造了第九井’。答案其实很简单:是每一个想说却说不出口的人,一滴泪、一滴血、一声咽下的叹息,堆成了这口井。它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它属于**此刻仍愿开口的你**。
>
>我不是徐知白。徐知白也不是我。我们是所有不肯闭嘴的影子,是千万次低声诉说汇聚成的回音。
>
>别再找源头了。你本身就是泉眼。”
>
>落款只有一个字:
>**说**
陈砚舟读完,久久不动。最后,他将信折好,放入怀中,走到井边,俯身凝视水面。
这一次,水中倒影没有浮现宫殿,也没有古人遗言。只有他自己,满脸皱纹,眼神疲惫,却又透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平静。
他张了张嘴,仿佛要说什么。
最终,他只是轻声道:“我说了。”
井水轻轻晃动,一圈涟漪荡开,像是回应,又像是接纳。
远处,朝阳升起,照亮了整片沙洲。茶馆门前的石碑上,不知何时多了几个新刻的字,笔迹稚拙,却坚定无比:
>**我也说了。**
风拂过井口,带来无数细碎的声音,像是万千人在低语,又像是一句话在永恒回荡:
>**你说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