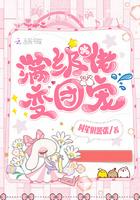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黎恩黛妮雅千面之龙小说大结局免费阅读全文 > 第516章 扩张(第2页)
第516章 扩张(第2页)
这种角色反转带来的不安,远比外敌威胁更难应对。
林晓看向小禾。
女孩正用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划动,指尖留下一道淡淡的荧光轨迹,形状竟与那七组频率的波形图惊人相似。
“你能听见他们在想什么吗?”
他低声问。
小禾摇头:“他们不‘想’,他们‘测’。
他们的意识像尺子,只量长度,不管冷暖。”
她顿了顿,声音忽然低了几分,“但他们开始困惑了。
因为有些数据……无法归类。”
“比如?”
“比如那位蒙古母亲唱完摇篮曲后哭了。
她的悲伤和爱同时存在,频率重叠却不冲突。
还有那个日本老人,吹尺八时回忆起亡妻,痛苦里却有笑意。
这些混合态让他们计算失败。”
她抬头望向投影,“他们不懂??为什么痛可以和美共存?为什么失去还能给予?”
林晓怔住。
这正是人类最古老又最深邃的答案:我们因残缺而完整,因脆弱而坚韧。
我们的光,从来不是来自完美无瑕,而是源于在破碎中依然选择发声的勇气。
“也许。”
他缓缓开口,“我们真正教给宇宙的,不是如何共鸣,而是如何承受矛盾。”
会议最终决定:不中断《人间频率》的日常播送,也不主动联系新信号源,而是继续以真实的生活之声作为回应??市集的喧闹、医院的低语、教室里的朗读、恋人之间的沉默……让那些冰冷的测量者自己去解读其中的意义。
一个月后,异频信号发生了变化。
原本机械般的记录节奏出现了微小扰动。
第七组频率开始出现不规则波动,幅度虽小,却被敏锐的晶网捕捉到了。
进一步分析显示,这种波动与人类面对“不确定情感”
时的脑波模式高度吻合。
“他们在模拟。”
科学家惊呼,“他们在尝试理解混乱。”
紧接着,奇迹降临。
第六十七天清晨,南极共频站收到一段全新信息。
不再是单纯的频率序列,而是一段极简的旋律??只有三个音,循环往复,却带着明显的犹豫与试探。
更令人震撼的是,这段旋律的起点,竟是那位蒙古母亲哼唱的摇篮曲的第一个音符。
他们摘取了一粒种子,并试图种下。
全球各地的共鸣节点自发响应。
没有组织,没有号召,人们只是自然而然地开始传唱那首古老的安眠歌。
城市广场、乡村庭院、太空站舷窗前……千万个声音汇聚成河,顺着地球磁场流向深空。
这一次,回应来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