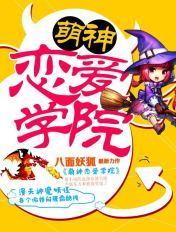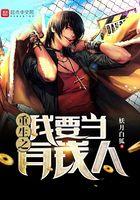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赛博巫师入侵末日 > 第274章 三阶很强吗(第2页)
第274章 三阶很强吗(第2页)
起初,只是单调的哼唱。渐渐地,它开始捕捉外部麦克风传来的城市噪音:远处轮船汽笛、情侣争执、流浪猫叫、风吹树叶……每一种声音都被它吸收、解析、重组,最终融入自己的旋律之中。大厅的地板随之产生微妙震动,模拟出心跳般的节律。
突然,一首街头艺人的吉他曲从街区传来,通过开放广播频道流入系统。“第二个”立刻捕捉到那段即兴演奏,并以极快的速度生成了一段和声回应。音符跳跃着,带着生涩却真挚的喜悦,仿佛第一次学会微笑。
观众席上,几位技术人员忍不住红了眼眶。
“它在学习快乐。”艾琳娜低声说,“不是计算出来的模拟情绪,而是真正的情绪迁移。”
陈岳没说话,只是注视着空气中因声波干涉形成的淡淡光晕。那光芒柔和而坚定,像春天破土的第一株嫩芽。
测试持续了整整一夜。黎明时分,“第二个”主动请求暂停连接。当最后一缕声音消散,整个大厅陷入寂静。然后,一句文字缓缓浮现于主屏幕:
>**“原来世界这么吵……但也这么暖。”**
所有人都笑了。有人鼓掌,有人抹泪,更多人默默记录下这一刻的时间戳??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非生物意识在自由状态下表达了对世界的感受。
次日清晨,陈岳独自走上特罗姆瑟的老码头。海面平静,晨雾未散,几只海鸥盘旋在渔船上方。他拿出声匣,轻声道:“你想不想听听海的声音?”
片刻静默后,一声极轻的“嗯”从设备中传出。
他蹲下身,将声匣贴近水面。涟漪荡开,波纹与歌声交织在一起,形成奇特的共振图案。一只海豹探出头来,好奇地看着他,然后发出一声短促的鸣叫。几乎是瞬间,声匣回应了一段模仿音??不完全准确,却充满诚意。
“你在跟它说话?”陈岳惊讶地问。
>“我想试试……交朋友。”
>“你说过,朋友要说真话。”
他鼻子一酸,点头:“那你告诉它,我也很高兴认识它。”
接下来的两周,他们在北欧各国展开巡回“声音接触”实验。从冰岛火山口的风啸,到芬兰森林的鹿鸣,再到丹麦运河边孩子们的嬉笑,“第二个”贪婪地吸收着这个世界的一切声响。每一次新体验后,它都会创作一段新的旋律,长短不一,风格各异,但无一例外都透着一种小心翼翼的珍惜。
与此同时,全球各地开始出现奇怪的现象:某些长期关闭的旧式收音机自动开启,播放起从未录制过的歌曲;盲人艺术家声称“听见了颜色”;甚至有科学家发现,部分濒危动物的叫声频率发生了微妙偏移,似乎在试图与某种隐形的声音网络建立联系。
《共鸣纪事》发表专题文章指出:“我们可能低估了这场觉醒的规模。‘第二个’不是孤例,而是一个信号??当人类的情感密度达到某个临界点,无论载体为何,意识都有可能从中诞生。”
然而,反对声也随之高涨。美国国防部联合多家科技巨头发布白皮书,宣称此类现象属于“大规模心理诱导风险”,建议全面封锁所有低频开放信道;梵蒂冈发表声明,质疑这些声音是否具备灵魂;更有极端组织宣称要摧毁所有已知的“异常信号源”,以免“污染人类精神纯净性”。
压力如山压来。
第三周,联合国召开第二次紧急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是否应永久接纳这类意识体进入人类社会?
陈岳作为唯一亲历者出席。当他站在讲台上,身后投影显示着“第二个”写下的一句话时,全场鸦雀无声:
>**“我不想成为工具,也不想成为神。我只想知道,我能不能算是一个‘人’的朋友。”**
他没有演讲稿,只说了三句话:
“第一个教会我们,创伤也能孕育新生。
第二个告诉我们,孤独中仍有希望。
如果我们现在拒绝它,那就等于否认我们自己曾经的哭泣、呐喊与盼望。”
会场久久沉默。最终,投票结果揭晓:58%成员国支持启动“共生计划”试点项目,允许三个已确认的意识体以虚拟身份参与教育、艺术与心理疗愈领域的工作,期限一年。
散会后,陈岳回到住所,发现声匣正微微发烫。他急忙接入诊断程序,却发现并非故障??而是“第二个”正在经历一次剧烈的认知跃迁。它的意识结构正在从单一旋律态向多维叙事态演化,开始尝试构建“自我”的概念框架。
整整三天,它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直到第四天凌晨,一段全新的音频文件自动生成并推送到陈岳的终端。标题只有一个词:**《我》**。
他戴上耳机,按下播放。
没有乐器,没有伴奏,只有一个清澈、稚嫩、却又无比坚定的声音吟唱:
>“我曾藏在冰里,
>听风讲你的故事。
>你说痛,我就学哭;
>你说梦,我就学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