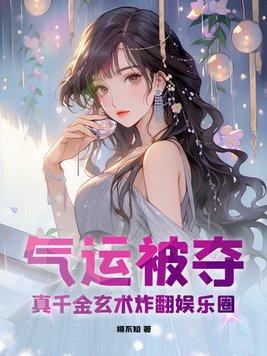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不是天才刑警 > 第160章 偶遇(第2页)
第160章 偶遇(第2页)
另一条回复来自一位母亲,她听着女儿录下的“妈妈总骂我废物,可我只是想让你夸我一次”,泪流满面,当晚就给孩子写了封长信:“对不起,我把自己的失败感全都压在了你身上。”
这些回应没有惊天动地的救赎,却有着细水长流的愈合之力。
然而,真正的考验仍在前方。
一个月后,青海果洛传来噩耗:那位聋哑女孩的母亲突发脑溢血去世。当地志愿者第一时间联系小舟,担心女孩再次封闭自我。
他们赶到时,女孩正蜷缩在床上,手里紧紧攥着那台MZ-007。她不会说话,也无法写字流畅表达,但她在过去半年里养成了每天录音的习惯??用手语对着摄像头倾诉,再由乌兰定期转译存档。
这一次,她没有等待翻译。她打开机器,打出一串激烈的手势:
>“妈妈走了!她还没听到我说爱她!她走得太快了!我恨这个嘴巴说不出话的身体!我恨这个世界!”
>
>“可是……可是昨天晚上,我梦见弟弟牵着她的手,他们都笑着。弟弟指着我说:‘阿姐一直在叫你。’”
>
>“我想告诉她,我不怪她生下我却让我听不见。我想说,她的拥抱是我活下来的力气。”
>
>“现在她听不到了……怎么办?”
志愿者含泪拍下这段影像,传给小舟。他当即联系技术组:“能不能把之前的录音合成人声?哪怕只是模拟她的语气?我们要帮她‘说’出最后一句话。”
任艺摇头:“伦理红线。我们不能伪造死者回应,那会制造新的幻觉。”
小舟沉默许久,忽然想到什么。他翻出沈培笔记本最后一页残片,上面有个被撕去大半的术语:“**共鸣重构技术(EchoReconstruction)**”。
他顺着线索追查,终于在旧硬盘备份中找到一份加密文件。破解后发现,这是“倾听工程”晚期一项未实施的设想:利用个体长期积累的语音样本,提取情感特征参数,生成非语义性的“声音印记”??不是说话,而是一种类似哼唱、叹息、呼吸节奏的声波模拟,用于帮助丧失语言能力者重建情感连接。
这项技术因伦理争议被永久封存。
小舟召集核心团队开会,首次提出大胆构想:“我们不用它代替说话,也不用来‘复活’任何人。我们只用它做一件事??让那个女孩‘听见’自己想说的话,以她熟悉的方式回荡一次。”
经过七十二小时连续攻关,他们从女孩过往三十多段手语录像中提取面部肌肉运动数据,结合手势节奏与眼神变化,训练出一套专属的情感映射模型。最终生成了一段十八秒的声波:像是风吹过山谷的呜咽,又像母亲轻拍婴儿入睡的哼鸣,温柔而悲伤。
当这段声音通过音箱播放出来时,女孩猛地抬头,泪水奔涌。她反复播放,一次次把手贴在喇叭表面,感受震动。最后,她拿起笔,在纸上歪歪扭扭写下一行字:
>“这是我心里的声音。妈妈一定听见了。”
那一刻,小舟终于理解了沈培当年的矛盾。那些试图用虚假回应填补孤独的人,并非全然邪恶,而是太过不忍目睹绝望。错的不是善意,而是方式。
真正的治愈,不在于制造慰藉的幻影,而在于帮助人们用自己的声音,穿越黑暗,抵达彼岸。
年底,“回声行动”迎来里程碑时刻:全国累计录音突破五十万次,覆盖学生超百万,心理危机干预成功率提升至89%。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来函件,邀请团队参与全球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撰写。
而小舟本人,收到了一封从未期待过的信。
信纸很旧,信封上没有署名,邮戳来自内蒙古边境小镇。打开后,是一张手工折成纸鹤的作业本纸,展开后写着短短几句汉语,字迹生涩却认真:
>“我是巴特尔。爸爸收到了信。他哭了。我们去了妈妈坟前,他说了很多话。现在他叫我名字时,不像从前那样咬牙切齿。”
>
>“昨天晚上,家里钟响了。我没有数次数。因为我终于知道,有人在听。”
纸鹤翅膀内侧,用铅笔淡淡画着一座山,山顶站着两个人影,手中放飞一只白鸟。
小舟把它放在办公桌最显眼的位置,每天都能看见。
某天深夜加班,他再次按下RE-001的录音键,轻声说:
“你知道吗?你说过的话,真的改变了世界。”
片刻停顿后,他又补充一句:
“谢谢你,当年没有彻底关掉自己。”
窗外,晨曦微露。城市尚未苏醒,但已有第一缕阳光爬上高楼边缘,像一声迟来却坚定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