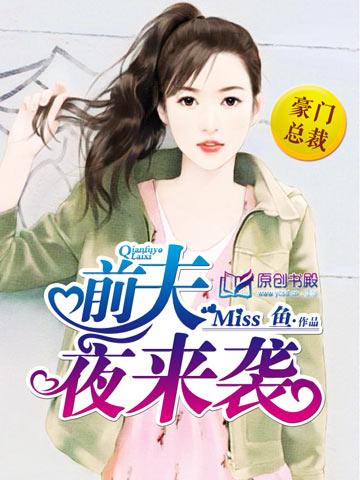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不是天才刑警 > 第153章 方向集中(第2页)
第153章 方向集中(第2页)
当天下午,首期“守夜人”招募公告发布。不到十二小时,报名人数突破八百。其中有退休护士、聋哑学校老师、癌症康复患者、出狱后重新生活的前帮教对象……每个人附上的申请理由都简短而沉重:
>“我女儿因抑郁跳楼前,最后一条语音没人听见。”
>“我在监狱听了三年别人的故事,现在想还这份债。”
>“我活下来,就是为了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发声。”
韩凌逐一审核资料,在一名叫李文秀的女子档案前停下。她是山区代课教师,丈夫死于矿难,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她在自述中写道:“去年冬天,班上有个女孩半夜烧炭轻生,被我发现时已经昏迷。抢救回来后她哭着说:‘我只是想试试,有没有人会来找我。’从那天起,我就知道,沉默比死亡更可怕。”
他批注:优先录用,安排心理督导支持。
与此同时,“记忆食堂”的影响力正向更多边缘群体渗透。第五个月,首个流浪者聚居点分站启动。地点设在城北废弃粮仓改造的空间内,每周五晚六点半准时开灶。菜单简单:一碗热汤面,加一颗卤蛋,外加四十分钟“今晚我想说”。
第一场活动来了九个人。有人讲自己如何因赌博输掉房子;有人说起儿子婚礼那天,他只能躲在远处树下偷看;还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妇人,颤抖着说:“我儿子在北京读博士,他不知道我现在睡桥洞。我不敢联系他,怕毁了他的前程。”
主持人是张建国,曾经的抢劫犯,如今已获假释并在社区做调解员。他听完所有人讲述后,只说了一句:“你们不是无家可归,是被人忘了名字。”
那一晚,九个人中八人留下了联系方式,表示愿参与后续互助小组。
而在疗养院旧址,一场特殊的重逢正在酝酿。韩凌根据照片线索,联合档案馆残存资料,终于拼凑出MZ-007项目的完整名单。除周素芬、林昭与陈国栋外,另有十七名研究人员曾参与早期实验,其中三人仍在本市。
他拨通其中一个号码。电话响了六声,即将挂断之际,传来沙哑女声:“喂?”
“请问是赵婉如医生吗?”韩凌尽量让语气平稳,“我是韩凌,关于1998年的心理干预项目……您还记得吗?”
对方长久沉默,呼吸变得沉重。“多少年了……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陈国栋先生临终前,留下了一些东西。”韩凌说,“我想知道真相,也为那些孩子。”
又是一阵停顿,随后,一声极轻的叹息:“我还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听到这个名字。”
三天后,他们在一家安静的茶馆见面。赵婉如已年过七旬,银发整齐挽成髻,眼神仍透着知识分子的锐利。她带来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数十页泛黄的手写笔记。
“我们最初的目标很简单。”她翻开第一页,声音低缓,“帮助遭受严重创伤的儿童重建情感连接。方法不是抹除记忆,而是重构叙述方式??让他们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讲述痛苦事件,并在安全环境中获得回应。这就是‘共感传递’的核心。”
她指着一段记录:“你看这个案例,F-05。五岁女孩,目睹母亲被家暴致死。她连续四个月不说一句话。我们让她每天对着录音机讲一个童话,不管逻辑是否通顺。两周后,她开始在结尾加上一句:‘公主最后找到了妈妈。’三个月后,她主动画了一幅画:两个女人牵着手站在彩虹下,写着‘她们都没死’。”
“这不是欺骗。”赵婉如抬眼看着韩凌,“这是心灵的自我修复。孩子知道自己在编故事,但他们需要一个出口,让压抑的情感得以流动。而当我们认真倾听,给予回应,那份流动便有了重量。”
韩凌翻阅笔记,发现每一例都有详细跟踪记录。许多孩子多年后回访显示,虽仍有心理波动,但具备更强的情绪调节能力和社会适应力。
“终止项目那天,我正在给F-14做第三次叙述治疗。”赵婉如声音微颤,“那是个被拐卖六年才找回的男孩。他刚说完‘我想恨爸爸,因为他没早点找我’,调查组就冲进来查封设备。我永远忘不了他脸上的表情??像是刚刚打开的门,又被狠狠关上。”
韩凌胸口发闷。他忽然意识到,MZ-007从未真正失败,它是被中断的黎明。
“你们后来怎么样?”他问。
“周素芬辞职后去了乡下,办了个留守儿童之家。林昭转行教心理学,专门研究倾听疗法。我提前退休,一直在社区做义务咨询。”她苦笑,“但我们都不敢提那段经历。媒体给我们贴上‘记忆操控者’的标签,家长视我们为怪物。可笑的是,如今你们做的‘声音档案馆’,本质上就是MZ-007的延续。”
韩凌怔住。
“你们没用药物,没建实验室,甚至没有理论框架。”赵婉如凝视着他,“但你们做到了最关键的一点??让人愿意说,也让人学会听。这才是真正的突破。”
分别时,她将笔记交给他:“这些不属于我,属于所有等待被听见的人。如果你继续走下去,请带着它们。别让历史再次沉默。”
当晚,韩凌彻夜未眠。他将所有资料数字化归档,并在内部系统建立“源流计划”专库,仅限核心成员访问。同时起草一份《共感伦理守则》,明确规定:绝不诱导叙述内容,不干预情绪表达,不利用故事牟利,始终保持倾听者的谦卑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