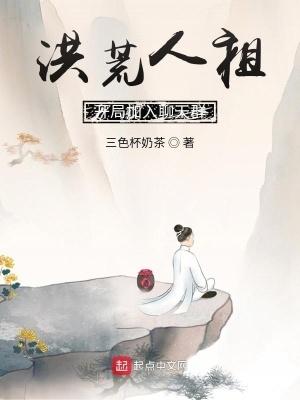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状元郎 > 第三七六章 一门三举人(第1页)
第三七六章 一门三举人(第1页)
都司衙门,千百只战靴交错,踏得校场上烟尘腾腾!
数十个白石灰圈依次排开,圈中武举考生各持一柄白杆枪捉对较量,辗转腾挪间使出浑身解数??有的白杆枪如灵蛇吐信,直刺要害!有的白杆枪如猛虎摆尾,横扫千。。。
春雨连绵,一连下了七日。屋檐下的水珠串成帘幕,敲打着青石阶,发出不疾不徐的节奏。苏家后园那块“感恩碑”已被雨水洗得发亮,字迹清晰如刻入骨血。金宝儿每日清晨必来碑前诵读一遍《孝经》,然后才去私塾。他如今已能背全《论语》,陈先生常在课上让他试作策论,虽稚嫩却有锋芒,引得族中长辈频频点头。
这日午后,天光微明,云层裂开一道缝隙,斜阳穿过梨树枝桠,洒在碑上“饮水思源”四字之上,竟似镀了一层金辉。七妮抱着药罐从厨房走出,忽见远处土路上来了三人:一骑快马在前,两名挑夫随后,肩上担着沉甸甸的木箱。
她心头一跳,忙迎上前去。
马上之人翻身下马,是个年轻驿卒,满脸风尘,拱手道:“可是苏府?此乃京师兵部加急文书,附弘之、春哥儿两位公子家书各一封,命亲手交付苏老太爷。”
七妮双手接过,指尖微颤。她知京师会试早已结束,殿试亦近尾声,这一纸文书,或许便是命运转折之始。
她疾步回府,直奔书房。老爷子正伏案校阅族中子弟文章,见她神色异常,立时起身:“可是京中信到?”
“是。”七妮将信递上,“加急文书,还有两封家书。”
老爷子深吸一口气,先拆开兵部公文。黄绢封皮上印着朱红大印,内文简洁庄重: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岁春闱取士三百六十一名,其中二甲第七名苏弘之,赐进士出身;三甲第八十九名李春,同进士出身。俱授翰林院庶吉士,候补实职。特此昭告乡里,以彰文教之盛。”
落款为礼部尚书兼殿试读卷官联署,日期正是半月之前。
老爷子读罢,久久无言,只觉胸口一阵热流涌动,眼眶骤然湿润。他缓缓坐下,手指抚过“赐进士出身”五字,仿佛触摸到了儿子三十年寒窗的冷灯孤影,春哥儿半生颠沛的坎坷行路。
“中了……都中了。”他喃喃道。
七妮喜极而泣:“爹!弘之进了二甲,将来有望入阁!春哥儿也登第了,咱们家真是祖坟冒青烟啊!”
老爷子却未笑,反是眉头紧锁:“越是如此,越要小心。”
他随即拆开弘之的信。信纸泛黄,墨迹略晕,显是仓促所书:
>“父亲膝下敬禀:儿幸不负所望,得列二甲。然殿试对策中直言盐政积弊,触怒户部某尚书,其党羽已在朝中散布谣言,谓我‘年少轻狂,不知轻重’。幸赖主考官力保,方免黜落。现虽入翰林,然步步如履薄冰。惟有谨言慎行,勤修典籍,不敢稍懈。
>春哥弟亦蒙恩录取,然因其策论批漕运贪腐,被指‘攻讦上官’,仅列三甲,授职待定。彼性刚烈,近日已有意辞官归隐,儿百般劝阻,终使其暂留京师。
>儿恳请父亲:切勿因儿等登第而改弦更张。家中田产不可扩,门第不可骄,族人不可恃势凌人。若地方再送匾额、献田产,请一律拒之门外。朝廷最忌士绅结党、豪强兼并,我苏家若稍有逾矩,必成众矢之的。
>又闻南党欲荐儿为主事,北党则密查我家底细,妄图寻隙构陷。故家中一切收支账目,务求清白可查,仆役不得逾十人,婚丧嫁娶不得逾制。若有亲朋借名谋利者,宁可断亲绝义,不可徇私姑息。
>儿夜夜梦回家园,见父亲独立碑前,心甚安。愿父保重身体,莫忧莫劳。儿纵不能日侍左右,然魂魄常归故里。”
信末附一小笺,乃是春哥儿亲笔:
>“岳父大人尊前:小婿惭愧,三十载漂泊,终得寸进。然此身已非自由之躯,一入仕途,便如棋子,任人摆布。我本布衣,志在天下清明,不料今日反需低头避祸。
>我妻仍居娘家,未曾归来,非我不念情义,实恐连累于她。若她携女归苏门,望善待之,视如己出。她抱养此女,乃一片慈心,非欺瞒之举。我已托人送些银两至其母家,聊作抚养之资。
>家规既立,万不可废。尤须提防族中有人假借我名在外行事。如有持我名帖者,皆为伪造,切勿接待。
>世道险恶,读书人若失了底线,比盗贼更可怕。望苏门子孙永记:功名是责任,不是特权。”
老爷子读完,双手颤抖,几乎握不住信纸。他闭目良久,才缓缓睁开,对七妮道:“把族人都叫来,祠堂议事。”
半个时辰后,苏氏男女老少齐聚祖祠。香火缭绕,烛光摇曳。老爷子拄杖立于祖先牌位前,声音低沉却如钟鸣:
“弘之、春哥儿皆已登第,入翰林,为国效力。这是苏家百年未有之荣。”
众人面露喜色,交头接耳,有人已按捺不住要放鞭炮庆贺。
老爷子猛然抬手,制止喧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