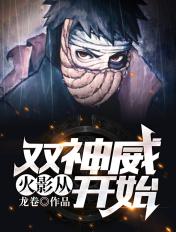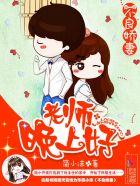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状元郎 > 第三七零章 同年(第3页)
第三七零章 同年(第3页)
杜陵补充:“此外,请开放部分盐铁专营权予民间商贾,引入竞争,降低物价,同时增加税收来源。如此,既可削垄断之弊,又能充盈国库。”
皇帝大悦,当即下旨:
“命礼部尚书李昭总理新政筹备事宜,都察院左都御史杜陵领衔监察体系重建,赐尚方宝剑一口,凡阻挠新政、贪赃枉法者,不论品级,皆可先斩后奏!”
诏书传出,满城震动。
然而风暴也随之而来。
当夜,李府门前突现匿名血书:“逆天改制者,必遭天谴!”
杜陵宅邸外墙被人泼漆,写着“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更有御史联名上疏,指控二人“结党营私,图谋不轨”,请求罢官治罪。
面对压力,李昭闭门不出,昼夜修订《义塾章程》,连发十七道公文,细化招生、师资、经费诸项规则,务求滴水不漏。
杜陵则亲自带队,突击巡查顺天府下属五县粮仓,当场查获三处常平仓空置率达九成以上,主官畏罪自缢。他毫不留情,将案卷呈报御前,并附奏折一篇:《论官场溃烂始于姑息》。
朝野为之哗然。
支持者赞其“铁面无私”,反对者骂其“酷吏重生”。
某日早朝,一位老尚书当庭痛哭:“二三十年太平岁月,毁于尔等激进之手!祖宗之法何在?纲常伦理何存?”
杜陵挺身而出,朗声道:“老大人,祖宗之法确在,但在《太祖实录》中写着‘养民如养子,怠则饥寒生’!如今百万流民露宿荒野,饿殍遍地,这才是对祖宗最大的不敬!若所谓‘纲常’只能维护权贵,不能庇佑百姓,那就不配称为纲常!”
满殿寂然。
皇帝最终拍案而起:“传旨:新政照常推行,任何人胆敢阳奉阴违,一律严惩不贷!李杜二卿,朕托付天下,勿负朕心!”
半年之内,新政初见成效。
全国丈量土地新增两千余万亩,税收增收三成;
三百余所义塾建成,十万贫童入学;
十五名贪官伏法,其中包括两名布政使;
南方盐价下降四成,百姓欢呼“活命之政”。
这一年冬天,京城下了第一场雪。
李昭与杜陵并肩走出宫门,雪花落在他们花白的鬓角上。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进贡院那天吗?”李昭忽然问。
“怎么不记得?”杜陵微笑,“你紧张得连砚台都打翻了。”
“那时只想着中举,光耀门楣。没想到后来竟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命运有时比文章更难预测。”杜陵望着漫天飞雪,“但有一点我很清楚??无论身处何位,我都不会忘记那个在破庙里抄书到咳血的自己。”
李昭点头:“我也不曾忘记,母亲织布的声音,是我听过最动人的读书声。”
他们走过长安街,远处传来孩童诵读之声:
“诚者,天之道也;勇者,人之责也……”
那是新编蒙学课本中的句子,出自双星堂碑文。
两人驻足倾听,久久未语。
多年以后,史官修《明史?循吏传》,记曰:
“李杜并起于寒微,同心佐治,锐意革新。其所行之政,惠泽深远,百姓至今称之。或问:何以能久持初心而不堕?答曰:因其始终不忘来路,故能不负去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