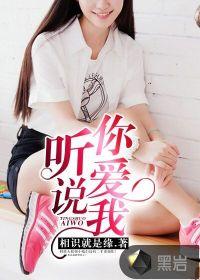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状元郎 > 第三六二章 捷报频传(第2页)
第三六二章 捷报频传(第2页)
“所以,”苏录目光坚定,“学生必须在乡试中夺魁,借此名望压服群议。”
“解元?”刘缨苦笑,“你以为这只是个名头?它是护身符,也是靶子。得了它,你便站在风口浪尖,万众瞩目,一举一动皆被放大。稍有差池,便会粉身碎骨。”
“学生愿赌。”
老人凝视他良久,终是轻拍其肩:“好,好。若天下读书人都如你这般清醒又敢拼,大明何愁不兴?”
马车辚辚驶出巡抚衙门,夕阳将影子拉得很长。
杨慎忽然冷笑:“你以为真能靠一篇文章赢天下?刘中丞临走都不支持你,你还妄想改天换地?”
苏录不理。
杨慎咄咄逼人:“你搞什么注音符号,废科举八股,裁巡抚,动藩镇,哪一样不是砸人饭碗?等你下场,我看你怎么活着走出贡院!”
苏录终于回头,直视着他:“用修,你说错了。我不是要砸谁饭碗,我是要让天下寒门子弟,不必再靠背诵范文、攀附权贵才能出头。我要的是??**人人皆可读书,字字皆能识得**。”
杨慎怔住。
苏录继续道:“你父亲可以一手遮天,可他挡不住民心所向。百姓看不懂告示,孩子念不起书,妻子读不了家书……这些痛苦,不会因为你们父子掌权就消失。而我做的每一步,都是为了让这世间少一点愚昧,多一点光亮。”
风起,卷起落叶扑向车窗。
杨慎嘴唇动了动,终是没有再说什么。
次日清晨,成都府贡院外鼓乐齐鸣,旌旗猎猎。
乡试正式开考。
考生们鱼贯入场,搜检极严,连发簪都要拔下查验。苏录走过龙门,抬头望见那块写着“惟楚有材”的匾额,心中默念:**此战,为千万不能言之人而战**。
第一场《四书》义题出乎意料??“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全场哗然。
此题看似平常,实则暗藏杀机。因“本”字可解为“祖宗成法”,亦可指“民生根本”。若偏向守旧,则落入苏录反对派圈套;若倡革新,则易触怒主考官中的保守派。
苏录闭目沉思片刻,提笔疾书:
>“所谓本者,非泥古之谓也。三代之礼乐刑政,因时损益,非尽沿袭。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可见‘本’者,在顺天应人,不在胶柱鼓瑟。今之所谓祖制,多为洪武初创,历经二百余年,田亩荒芜,户口流离,赋役繁重,边患频仍。若拘泥旧章,是抱火寝薪而不觉也……”
文至半篇,已有考官低声惊叹:“胆大包天!”
另一人却抚须点头:“理正辞严,确有见识。”
到了第三日,消息悄然传出:首场头名答卷,竟是苏录所作,且主考官拟列为“超等”。
与此同时,杨慎的文章也被传抄出来,题为《守先待后论》,主张“改制不毁纲常,更张不忘根本”,虽未直接反驳苏录,却隐隐划清界限。
两篇文章如同双峰并峙,震动全城。
街头巷尾,士子争辩不休。有人赞苏录“开千古未有之新局”,也有人骂他“离经叛道,惑乱人心”。更有匿名揭帖贴满城墙:“苏录欲废圣贤之学,改易祖宗之法,其心可诛!”
第七日,第二场策问卷发下。
题目赫然是:“论川省巡抚存废利弊。”
全场死寂。
谁都明白,这是冲着苏录来的。
苏录握笔的手微微一顿,随即展纸挥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