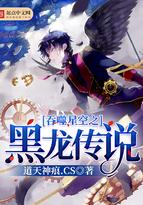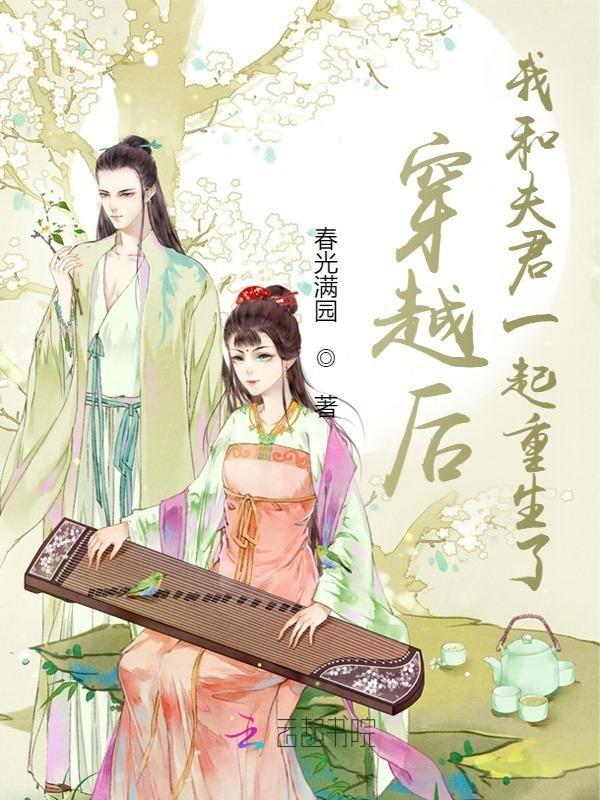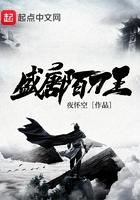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状元郎 > 第三五九章 卧龙凤雏(第3页)
第三五九章 卧龙凤雏(第3页)
“难怪王阳明辞官赴黔,原来是为了栽培此子!”
更有好事者细看榜单,发现苏录不仅四书文列优等,五经文亦被评为“超等上”,两项皆居榜首,实属罕见。
而在榜单末尾,王阳明的名字赫然在列,等级为“中等”,虽未被淘汰,却也无缘优贡。
消息传回家中,王阳明躺在床上听完通报,先是沉默,继而哈哈大笑,笑得咳嗽不止,眼角渗出泪水。
“好!好!好!”他连说三声,握紧苏录的手,“我这辈子最得意的事,不是中进士,不是做官,而是生了你这个儿子!如今你已青出于蓝,我纵然明日死去,又有何憾!”
苏录跪地叩首,泣不成声。
当晚,常厚纨再次登门,这次带来了正式文书。
“恭喜你,苏弘之。”他郑重宣布,“经本官复核,你两场成绩均为最优,特准予‘优贡生’资格,无需参加乡试预选,可直接赴成都府参加九月秋闱。”
顿了顿,他又低声补充:“而且……我已经把你这篇文章呈报布政使司,甚至有可能推荐入京,参与明年会试的‘观政进士’选拔。”
苏录震惊抬头:“学生资历尚浅,岂敢妄想如此殊荣?”
“这不是妄想。”常厚纨目光灼灼,“这是天意。当今朝廷正值变革之际,内阁有意提拔一批年轻才俊,打破旧党垄断。而你这篇文章,恰好击中了他们的痛点??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只会背书的腐儒,而是一个能说出新话、扛起道统的年轻人。”
他压低声音:“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担心太过张扬,会招来嫉妒。但你要明白,有时候,锋芒毕露也是一种保命之道。只要你站在风口浪尖,别人反而不敢轻易动你。”
苏录默然良久,终于点头。
数日后,王阳明病情稍缓,勉强能拄杖行走。一家人齐聚庭院,商议秋闱准备事宜。
苏录提出欲前往成都提前温习,结交各地英才。
苏满表示愿同行照料。
苏淡则打算留在泸州照顾父亲。
正在商议间,忽有驿卒送来一封急信。
拆开一看,竟是萧提学亲笔:
>“弘之吾徒:
>得悉汝科试夺魁,欣慰之至。龙场瘴疠之地,竟育此良苗,足证心学不虚。然须知,科名不过是敲门砖,真正的大考,还在后头。
>秋闱在即,我已为你谋得一处静修之所??成都北郊昭觉寺,住持乃我旧识,可容你闭关月余。届时,我亦将亲赴成都,与你面授机宜。
>切记:临文勿求工巧,但求真诚;应试勿计得失,但问本心。
>若能持此信念入闱,纵使不中,亦不失为豪杰。
>师萧某手书”
众人读罢,无不肃然。
苏录捧信于胸前,面向北方深深一拜。
他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而在这条通往圣贤的路上,他已无法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