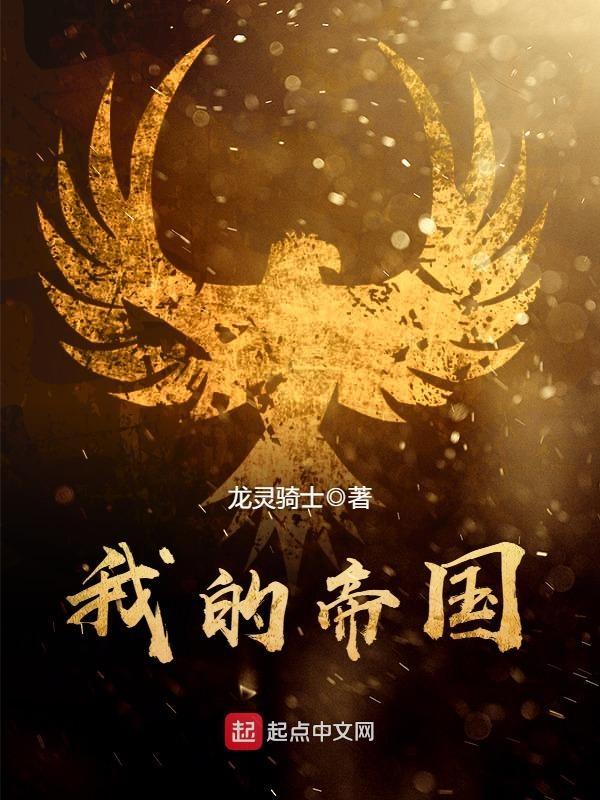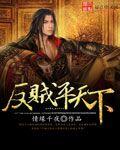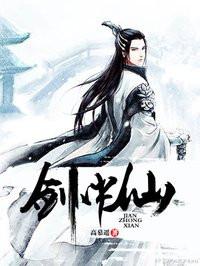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状元郎 > 第三五五章 乡试(第2页)
第三五五章 乡试(第2页)
自此,“南有贵阳,北有遵义,中有播州”之说渐起。朝廷亦不得不承认,这片曾经被视为化外之地的边陲,如今已是西南文教中心。
岁月流转,杨氏家族七代相传,始终严守祖训:每代土司必入阳明书院修业三年,不通心学者不得执政;每岁必派子弟赴中原游学,带回新书、新技术;凡境内发生命案,必须经书院与衙门共审,确保“情理法”三者兼顾。
到了万历末年,朝廷为加强控制,推行“改土归流”,废除世袭土司,改派流官治理。诏书下达之日,举国震动。其他土司或起兵抗命,或潜逃山林,唯独播州平静如常。
时任土司杨允敬率全族赴贵阳接旨,叩首受命,毫无怨言。返程途中,幕僚不解:“主公为何不争?百年基业,就此断送?”
杨允敬微笑道:“争什么?权力从来不是我们的目的。祖父说过,低头是为了看清路。如今朝廷愿以礼法治此地,正是我们多年所盼。若仍恋栈不去,反倒违背了良知。”
于是,播州正式纳入国家行政体系,设遵义府。原土司府改建为“守仁总祠”,供奉杨斌、王阳明及历代杨氏贤主牌位。阳明书院升格为“黔中学院”,成为全省最高学府。
即便失去爵位,杨氏子孙依旧深受百姓敬重。每逢灾荒,他们率先捐粮;每逢战乱,他们组织义学避难;每逢科举,他们资助贫寒学子。民间传言:“杨家无官,胜似有官。”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覆亡。南方各地拥立福王、唐王、桂王相继称帝,彼此攻伐不断。西南诸省再度陷入混战。
此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拄杖登上望云峰,正是当年那个接过《传习录》的孩童??如今已年逾古稀的杨氏第八代嫡孙。他望着远处战火映红的天际,轻声对身边孙儿说:“爷爷曾问你什么是文明,你还记得吗?”
孩童点头:“记得。是靠说话解决问题,相信道理最真,把别人当朋友。”
老人颔首,从怀中取出那本早已破损泛黄的《传习录》,轻轻翻开,指着其中一页道:“你看,这里写着‘良知即是非之心’。是非不在胜负,而在是否利民。不管天下怎么变,只要我们守住这个,就不怕黑暗长久。”
他合上书,仰望星空:“王阳明先生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我们不能决定时代,但可以决定自己的心。只要还有人在读这本书,在信这个理,在做这件事,文明就不会灭亡。”
翌日,他在黔中学院召集所有师生,宣布成立“明道社”,宗旨为“存亡继绝,守护斯文”。无论政权更替,社团永不解散,每年清明必祭王阳明与杨斌,每月朔望必讲《传习录》,每逢乱世必收容流亡士人。
清军入关后,多尔衮下令焚毁一切“异端邪说”,尤其严禁阳明心学传播。许多地方书院被迫关闭,典籍付之一炬。唯有黔中学院以“讲授农桑技艺”为名,暗中保存全套心学文献,并将《传习录》内容改编为童蒙读物,如《小儿良知歌》《耕读二十四则》等,借识字课悄然传授。
顺治十年,清廷察觉苗头,派御史赴贵州彻查。御史翻遍全院藏书,只见农书、医册、算经,不见一部“狂悖之书”,只得悻悻而归。临行前,院长恭送至山门,递上一卷手抄本,笑道:“大人远来辛苦,此乃我院编纂的《山居养生法》,内含静坐调息之术,有益身心,敬请笑纳。”
御史打开一看,竟是《致良知说》全文,用养生术语重新诠释,如“静坐者,非止息念,乃觉察本心之光明也”。他苦笑摇头:“罢了罢了,你们赢了。”
康熙初年,天下渐定。新帝重视文教,开博学鸿词科,广征天下遗贤。黔中学院先后推荐十三人应试,皆高中,其中二人入翰林院。京师为之震动,称“西南文气,尽出播州”。
康熙皇帝特召杨允敬之孙杨维桢入宫问对。君臣谈及王阳明,杨维桢直言:“阳明先生之学,不在空谈性命,而在经世致用。他教人明白一点: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盏灯,只要肯点亮,就能照亮自己,也能温暖他人。”
康熙默然良久,叹道:“朕读朱子书多年,今日方知另有大道。”遂下诏恢复阳明从祀孔庙,追赠“文成”谥号,并命将《传习录》列入官学教材。
消息传至播州,全城焚香燃烛,百姓自发聚集守仁祠前,齐声诵读“心即理也”四字。那一夜,雷雨交加,电光劈开乌云,直落书院屋顶,屋脊兽首忽现青焰,久久不熄。守夜人跪地泣告:“先生回来了!”
自此后,每逢风雨之夜,附近村民皆闻朗朗诵书声自祠中传出,清晰可辨。有人说是孤魂野鬼,有人说是幻觉,唯有孩童坚信不疑:“那是王爷爷在教书呢。”
时光荏苒,大清衰微,民国建立,战火再起。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西迁遵义,借用黔中学院旧址办学。竺可桢校长巡视校园时,见石碑上“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八字,久久伫立,感慨道:“昔阳明先生处贬谪之困而开万世之智,今我辈逢国难之际,岂能不效其精神?”
遂在此设立“求是讲堂”,每日晨钟暮鼓,师生共读《传习录》,誓言“读书不忘救国,明心方可报国”。
一位年轻学生写下日记:“昨夜空袭警报响起,众人奔逃。我回头看见一位老教授抱着一摞书不肯走,他说:‘这些东西比命重要。’后来才知道,那是明代刻本的《阳明全书》。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什么叫文化的脊梁。”
抗战胜利后,浙大东归,临行前将一面锦旗赠予学院,上书:“薪火相传,道脉不绝。”
如今,昔日播州之地已成为遵义市的一部分。阳明书院几经修缮,辟为纪念馆,每日游客如织。孩子们在碑前背诵课文,大学生在此写生摄影,外国学者专程前来研究心学传播史。
但在某个深夜,若有行人经过书院围墙,或许会听见风中传来低沉的诵读声: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声音悠悠,仿佛穿越了五百年的风雨,依然坚定地诉说着一个信念:
只要人心不死,光明就永远不会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