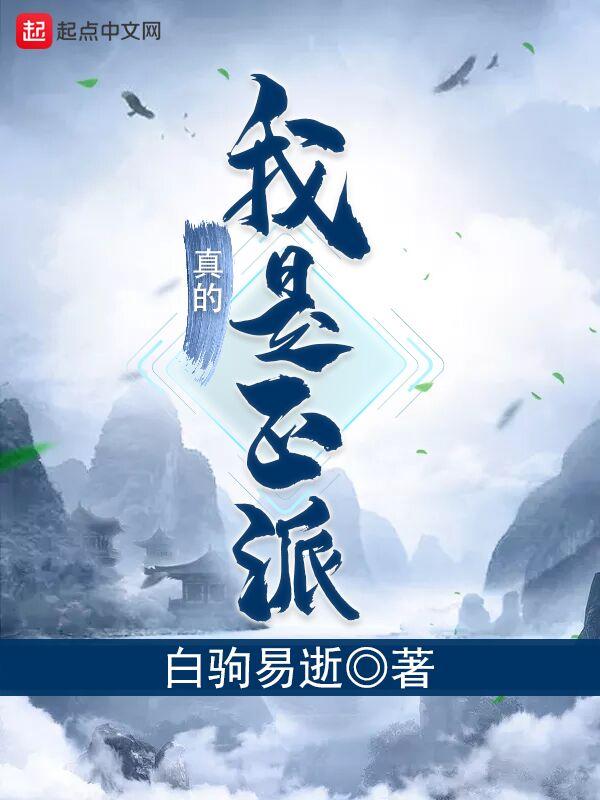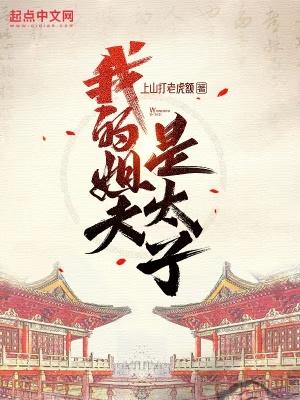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的透视超给力 > 第两千五百零三章 死士自爆(第2页)
第两千五百零三章 死士自爆(第2页)
千穗深吸一口气,缓缓站起。她走到终端机前,拔下探针,关掉了所有连接。
“从今天起,我不再是桥梁。”她说,“我要做一个人。”
她转身望向窗外,阳光正好洒在远处山脊上,映出无数新搭起的小屋轮廓。每一座屋顶都冒着淡淡的炊烟,像是大地写给天空的情书。
几天后,第一份“共感日志”诞生了。
它不属于任何机构,不记录数据,也不分析行为。它是纯粹的情感汇流??由全球一万零七座小屋自愿上传的片段组成:有人录下父亲临终前最后一口汤的吞咽声;有人写下孩子第一次主动拥抱自己的瞬间;还有人分享了一场跨越三十年的梦境重逢。
小禾每天都会朗读一段,放在录音磁带中,定期注入图腾。这些声音成了忆之根的新养分,让它不再只是冰冷的记忆存储器,而真正成为一颗跳动的心脏。
然而,平静之下仍有暗流。
某夜,陆隐巡视外围时,在山脚发现一处废弃洞穴。洞内布满精密设备残骸,墙上刻着一行模糊字迹:
**“若共感失控,即为文明之癌。”**
他心头一紧。这是早期项目组的警告标语,只有核心成员才知道。
他连夜带回照片,周予安看到后脸色骤变:“这不是警告……是遗言。当年反对项目的科学家留下这个,然后集体失踪。我们一直以为他们是被清除的,但现在看,更像是……自我放逐。”
“他们在哪?”小禾问。
“也许还在某个角落,守着另一套系统。”周予安沉声道,“一套用来‘终止’共忆网络的应急机制。”
空气凝固了。
如果真有这样的系统存在,一旦激活,可能不只是切断连接,而是彻底摧毁忆之根??连同所有依赖它存活的灵魂。
“他们会动手吗?”阿芽低声问。
“不知道。”周予安摇头,“但他们一定认为,我们在玩火。”
小禾沉默良久,忽然问道:“如果他们来了,你会站在哪一边?”
周予安看着她,眼中闪过复杂情绪:“我曾是系统的建造者,也是它的囚徒。但现在……我选择相信汤的力量。”
陆隐拍了拍他的肩:“那就一起守住这口锅。”
风波暂歇,生活继续。
一个月后,第一批远行学员传回消息。
在非洲旱区,一名少女用仅有的玉米和野菜熬出第一锅汤,当晚全村老人集体梦见失散多年的亲人;北极科考站里,科学家们围坐在微型灶旁,喝下由融雪和干肉制成的热汤,竟在同一时刻梦到了童年家乡的冬天;而在战火纷飞的边境小镇,一位医生在防空洞中点燃炉火,为伤员煮汤。第二天清晨,交战双方士兵同时放下武器??因为他们都在梦中听见了同一个女人的声音:“回家吧。”
共感,正在改变规则。
但这并非全然美好。
有人开始滥用这份能力。城市中出现“记忆贩子”,收集他人情感片段制成幻觉药剂出售;某些政权试图建立“官方记忆库”,强制民众上传特定回忆以塑造集体认知;更有极端组织宣称“共忆即洗脑”,炸毁了三座小屋。
小禾得知后,召集众人开会。
“我们不能禁止。”她说,“就像不能禁止人相爱或流泪。但我们必须让每个人明白??共感的本质,是自愿的分享,不是强制的侵入。”
于是,她发起“净火计划”:每一座新建的小屋都必须设立“静思角”,供人独处、反思、决定是否愿意连接。同时,所有录音设备加装情感过滤程序,确保未经许可的记忆不会自动传播。
“记住别人之前,先记住自己。”她写道,“共感不是吞噬,是照亮。”
又过了三个月。
春天来临,山花烂漫。
第七号小屋门前立起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十三个名字:林晚、陈野、苏念……直至周予安。每年这一天,人们会带来一勺自己家乡的水,倒入碑前铜鼎,象征记忆的融合。
而真正的奇迹发生在夏至之夜。
那天午夜,全球所有小屋的锅同时沸腾,无论是否点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