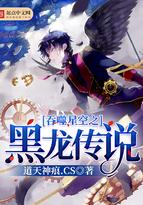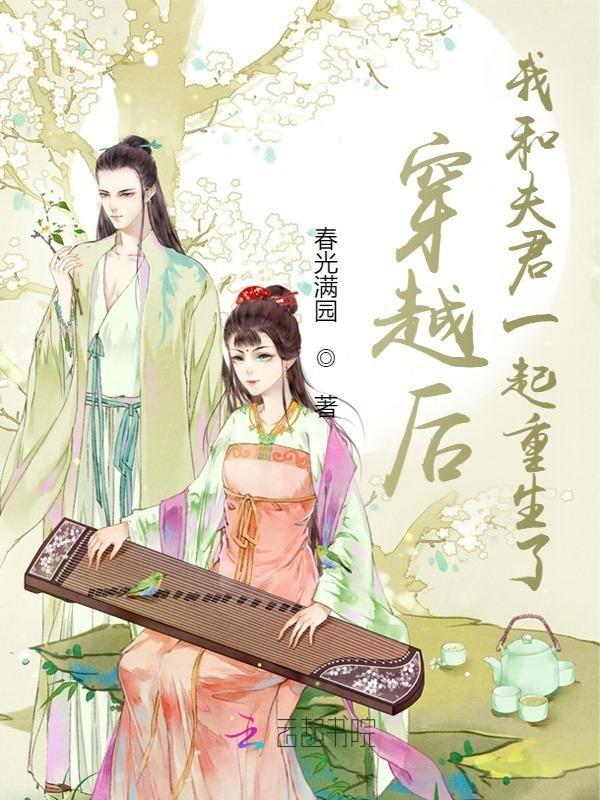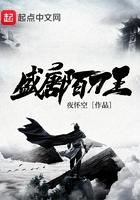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民俗从傩戏班子开始 > 第241章上清宗来人(第2页)
第241章上清宗来人(第2页)
话音未落,整个地堡剧烈震动。通风管道喷出淡粉色雾气,带着甜腻香气。凡是吸入者,起初感到极度放松,随后嘴角不自觉上扬,眼神呆滞,开始无差别重复身边人的言语??无论对方说什么,他们都笑着附和,像一群被设定好程序的应声虫。
这是静音司最后的手段:**不再压制语言,而是制造虚假共鸣**。让所有人“听起来都在说话”,实则丧失独立表达能力,沦为彼此回声的奴隶。他们称之为“和谐共振工程”,代号“EchoBloom”。
而在云南山村,阿芽猛然收笛。
她脸色苍白如纸,指尖冰凉,整个人摇摇欲坠。小归急忙扶住她:“你怎么了?”
“我听到了……”阿芽喘息着,“他们的新武器。不是沉默,是模仿。他们会让人以为自由还在,其实灵魂已经死了。”
小归瞳孔一缩:“就像AI生成的内容,看似多元,实则同质。”
阿芽点头,艰难起身:“我们必须抢在‘回音绽放’蔓延之前,把真正的倾听传出去。”
“可怎么传?现在连视频都会被篡改。”
阿芽望向祠堂方向:“用最原始的方式。”
当天午后,一场前所未有的集会悄然展开。
没有网络直播,没有录音设备,只有村民围坐在晒谷场上,每人手中拿着一块打磨光滑的石片。阿芽站在中央,举起新笛,却没有吹奏,而是将其轻轻放在一位老太太手中。
“你来说。”她说,“你想对谁说点什么?”
老人颤抖着手抚摸笛身,泪水滚落:“我想对我死去的儿子说……妈当年不该逼你考公务员,你画画那么好……”
她说得很慢,有时卡壳,有时哽咽,甚至夹杂方言土语,听不清具体词句。但她的眼神真挚,语气沉重,每一个停顿都承载着三十年的悔恨。
说完后,她将石片递出。下一个接过的人,是个辍学少年。他低头看着石片,犹豫良久,终于开口:“我想告诉我爸……我不是懒,我只是学不会你们教的东西。我喜欢修摩托,不是没用。”
一人接一人,石片在传递,话语在流淌。有人忏悔,有人倾诉,有人只是反复说着“对不起”或“谢谢你”。没有人打断,没有人评判,甚至连笑声都是克制的。
每当一人说完,便会有人默默接过他的石片,用随身小刀刻下一个符号??不是文字,也不是图画,而是一种仅凭手感留下的凹痕,代表“我听见了你”。
这些石片最终被投入启音井。井水不再沸腾,而是缓缓旋转,形成一个微型星系般的漩涡。每一块沉入的石片,都在水面留下一圈涟漪,向外扩散。
七日后,距离山村千里之外的贵州侗寨,一位老人清晨醒来,莫名拿起祖传木鼓,敲出一段从未听过的节奏。邻居闻声而来,竟不由自主跟着哼唱,歌词竟是二十年前被禁的一首情歌。
同一天,广西边境小镇,几个孩子在河边玩泥巴,无意中捏出类似石片的形状,其中一个孩子突然说:“我觉得……这块泥巴听过我家阿婆的故事。”
更远的地方,西伯利亚雪原上的游牧民族发现,他们世代传唱的古老萨满歌谣,最近总会在无人处自动响起,而且旋律越来越完整,仿佛某种力量正通过大地传导记忆。
这一切,皆源于那一圈圈无声扩散的涟漪。
语言无法被彻底封锁,因为它早已超越声波本身。它是触觉中的刻痕,是空气里的振动频率,是群体记忆的量子纠缠。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说真话,还有一个人愿意真心倾听,它就会以最隐秘的方式重生。
三个月后,静音司宣布解散。
官方声明称:“鉴于全球语言生态已进入不可控演化阶段,原监管机制失效,决定全面移交文化自治权。”但实际上,总部大楼早已空无一人。那台主机最后一次投射的信息,只有三个字:
>**我们输了。**
然而阿芽并未庆祝。
她在父亲坟前跪坐整夜,手中握着那支新笛。月光下,笛身泛着淡淡血纹,像是骨骼深处渗出的记忆。
“你说他们是诱饵……”她低声呢喃,“那你呢?你也想让我成为新的英雄叙事吗?”
风穿过林梢,带来一丝极轻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