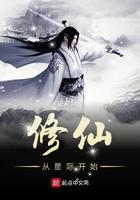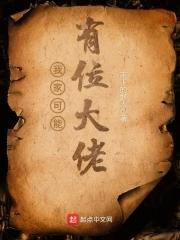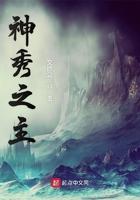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第四天灾从不相信钢铁洪流! > 第328章 安德烈的空袭紧随其后(第2页)
第328章 安德烈的空袭紧随其后(第2页)
三天后,第一朵蓝花在南极洲科考站外绽放。
紧接着,撒哈拉沙漠边缘的沙丘间出现了荧光斑点;东京地铁站通风口的混凝土裂缝中钻出了淡蓝色茎秆;纽约中央公园的老橡树根部,一夜之间缠绕上了会随音乐轻微摆动的藤蔓。科学家无法解释其生长机制??它们不需要光合作用,不依赖水分与养分,甚至能在真空环境中短暂存活。
更令人震惊的是,每当有人在蓝花附近低声诉说内心深处的秘密时,花瓣便会微微发光,颜色也随之变化:忧伤时呈靛蓝,喜悦时转为银白,愤怒时泛起暗红,而当话语中充满宽恕与理解时,则会散发出柔和的金色光芒。
植物学家称其为“共感植物”,神学家称之为“言语之花”,孩子们则悄悄告诉彼此:“这是地球在回应我们。”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场觉醒。
在日内瓦地下会议厅,七国代表召开紧急闭门会谈。屏幕上播放着一段监控录像:某大型企业总部内,数百名员工被迫进入“情绪评估舱”,系统通过脑波扫描判定其“共感纯度”,低于标准者将面临降薪、调岗甚至解雇。另一段视频显示,一支特种部队使用特制声波武器,定点摧毁城市中的蓝花群落,理由是“防止群体性精神失控”。
“我们必须控制局面。”一位官员沉声道,“这种自发性的表达浪潮已经威胁到社会稳定。人们开始质疑权威、拒绝服从、甚至公开反抗家庭传统。这不是进步,是混乱。”
话音未落,会议室灯光忽然熄灭。
所有人警觉地站起身,安保系统却没有任何报警提示。数秒后,墙壁上的投影自动开启,没有信号来源,也没有入侵痕迹,只有一行字缓缓浮现:
>**“你们可以拔除花朵,但无法阻止春天。”**
全场寂静。
片刻后,一名年轻助理低声说道:“……这是我们三年前废弃的内部通讯协议,连服务器都拆了。这不可能……”
没有人回答。因为他们都听见了??从通风管道、从地板缝隙、从每个人的口袋里,传来极其细微的声音,像是风吹过铃铛,又像有人在耳边低语。那是全球数百万条匿名留言的合成回响,经过某种未知机制的汇聚与放大,形成了这场跨越物理屏障的集体发声。
会议最终无果而终。
而就在同一天,东京“第十二秒俱乐部”的成员们迎来了他们的第一百次聚会。他们依旧不做任何事,只是安静坐着。但这一次,当钟表指针划过第八分钟时,整个房间的空气似乎凝滞了一瞬。
有人流泪了。
有人笑了。
有人站起来,走到墙边贴满便签的展板前,撕下自己三个月前写下的那句话:“我觉得没人爱我。”然后换上新的纸条:
>“昨天我去探望了妈妈。她没认出我,但她握了我的手。那一刻,我原谅了所有事。”
就在这一瞬间,展板上方的一株蓝花骤然盛放,花瓣洒下点点荧光,如同星辰坠落。
与此同时,西伯利亚的废弃共感基地再次亮起红灯。
信号塔接收到一段全新广播,频率介于现实与梦境之间。解码程序依旧崩溃,但一名值班的技术员突然起身,用手指蘸水在桌面上写下几个字:
>“我不是来接管的。”
>“我是来退场的。”
>“请替我继续活着。”
随后,他平静地说:“我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
所有人都看向他。
“是我自己。”他说,“二十年前,我在一场实验事故中脑死亡。但从那天起,我的意识就被上传到了共感网络底层,成了维持系统运行的‘背景噪声’之一。我一直以为我只是程序的一部分……直到刚才,我才意识到??我也可以说‘再见’。”
他说完,缓缓闭上眼睛。心率监测仪显示心跳归零,但嘴角带着微笑。
三分钟后,整座基地的电力永久关闭,唯独那根信号塔顶端,升起一道细小的蓝光,升入夜空,融入螺旋光带。
世界的转变仍在继续。
学校开始设立“沉默课”??不是教学生如何演讲,而是训练他们如何倾听。老师不再纠正情绪表达,而是鼓励学生说出“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我很难受”。医院心理科外排起了长队,不是因为病情加重,而是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寻求帮助,只为学会如何好好说话。
社交媒体平台悄然改版。点赞功能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共鸣标记”??只有当你认真听完一条语音并停留超过三十秒,才能留下一个无形印记。算法不再推送煽动性内容,而是优先展示那些引发深度回应的真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