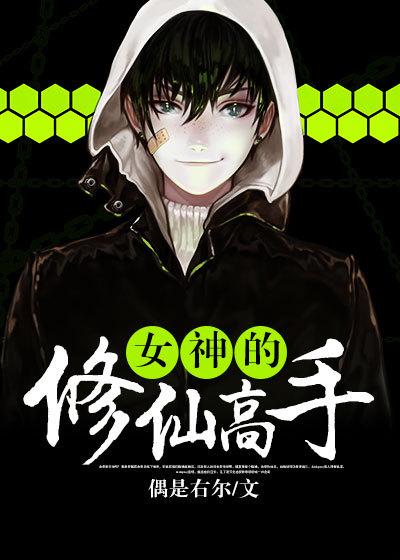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坦坦荡荡真君子 > 第452章 你是最特殊的(第1页)
第452章 你是最特殊的(第1页)
镜中的陆轩相当年轻,也是就二十三四岁的模样,眉眼间还带着未褪尽的青涩。
当林晓已经知道了,陆轩是自己的“前辈”之一后,他立刻意识到了陆轩的牺牲和付出有多么大。
以往的每一代“前辈”们,哪怕。。。
林晓微微一笑,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最后落在罗海身上:“你问我怎么得出来的?其实很简单??我用了你们的数据,但换了一个角度。”他顿了顿,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你们计算的是制度运行的资源消耗降低了多少,而我计算的是人在这种制度下的‘痛苦产出效率’下降了多少。”
他缓缓从怀中取出一本薄册子,封面上写着《苦痛之力行为模型初探》几个字。不少人认出那是最近在司祭院内部流传的一份非正式报告,作者署名正是“林晓”。
“我在三个月前就开始研究一个问题:一个人在感受到幸福时,能承受多少痛苦?而在失去希望、对未来毫无期待时,又能承受多少?”林晓翻开册子,指着其中一页图表,“这是我收集的三百七十二个样本数据汇总。包括战俘、矿工、修行者闭关记录,甚至还有自愿参与实验的志愿者。”
台下有人低声惊呼:“三百多个真实案例?这工作量……”
林晓继续道:“结果很明确??当个体处于‘当下幸福+未来可期’的状态时,其单位时间内产生的苦痛之力,比‘当下痛苦+未来无望’状态高出平均63。4%。注意,这是净产出,已经扣除了维持生命与基本运转所需的最低消耗。”
罗海眉头紧锁,迅速在脑海中演算着这个数字对原方案的影响。他原本假设的是系统性节流带来20%的整体优化,但如果苦痛之力的产出直接暴跌六成以上,那别说正收益了,连维持现有供给都成问题。
“等等!”罗海突然抬头,“你说的是‘平均’?有没有可能某些群体不受影响?比如军人、执法者、红袍序列本身?我们这些人早就习惯了压抑情感,追求秩序高于一切!”
林晓点点头:“你说得没错,确实有一部分人适应了高压与牺牲。但你要明白一点??整个国家不可能由红袍序列组成。你所谓的‘第三国制度框架’,是要覆盖全体国民的。而大多数普通人,并不具备你们这种训练有素的心理素质。”
他转向观众席:“请问,在座各位,有多少人能在连续三年看不到晋升希望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工作效率不下降?又有多少人能在明知自己孩子将继承贫困、终生无法摆脱底层命运的前提下,还愿意为国家拼命?”
没有人回答。沉默本身就是答案。
林晓轻声道:“我们不是在设计一台机器,而是在构建一个社会。机器坏了可以更换零件,但人心一旦熄灭,就再也点不燃了。”
这时,一直沉默的墨衡忽然开口:“所以你的意思是,罗海的方案错不在逻辑推导,而在于忽略了最关键的变量??人性?”
“正是如此。”林晓合上册子,“他们把人当成恒定不变的资源处理器,仿佛只要输入足够的压迫和纪律,就能稳定输出苦痛之力。可现实是,人的情绪、信念、希望,才是决定产出的核心因素。就像一块土地,你不断收割却不施肥,终有一天会荒芜。”
林锋喃喃道:“难怪老大最近总说,真正的统治不是控制,而是引导……”
场上气氛渐渐凝重。原本以为只是一场技术性的政策辩论,没想到竟触及了治国理念的根本分歧。
罗海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就算你说得有道理,那你又能提出什么更好的方案?否定别人很容易,但建设才是最难的。如果你没有替代方案,那这一切讨论都没有意义。”
这话问得很狠,直指要害。
林晓却没有立刻回应,而是环视四周,仿佛在确认什么。片刻后,他才缓缓说道:“我知道你们一直觉得我是个理想主义者,甚至有人说我天真。可我想告诉你们??我不是反对制度,也不是反对牺牲,我只是反对那种把人民当作燃料烧尽的制度。”
他抬起头,眼神坚定:“所以我提出的方案,叫做‘双轨制重构计划’。”
全场一静。
“所谓双轨制,是指在同一片国土上,建立两种并行的社会模式。”林晓展开一张地图投影,上面清晰地标出了南北两区,“北部保留现有的红袍管理体系,强化镇压机制,用于应对紧急危机和外部威胁;而南部,则试点开放‘希望激励体系’。”
“希望……激励?”有人疑惑地重复。
“对。”林晓点头,“简单来说,就是让一部分人先看到未来。通过教育、晋升通道透明化、家庭福利保障、文化复兴等方式,重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预期。只要他们相信努力会有回报,痛苦就会转化为力量。”
“这不就是变相鼓励享乐主义吗?”一名年长司祭皱眉质疑,“一旦人们开始追求幸福,谁还愿意承受痛苦?苦痛之力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