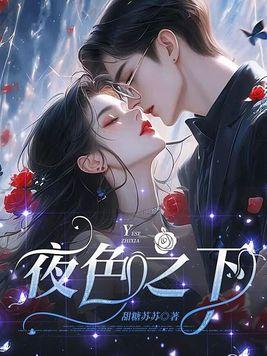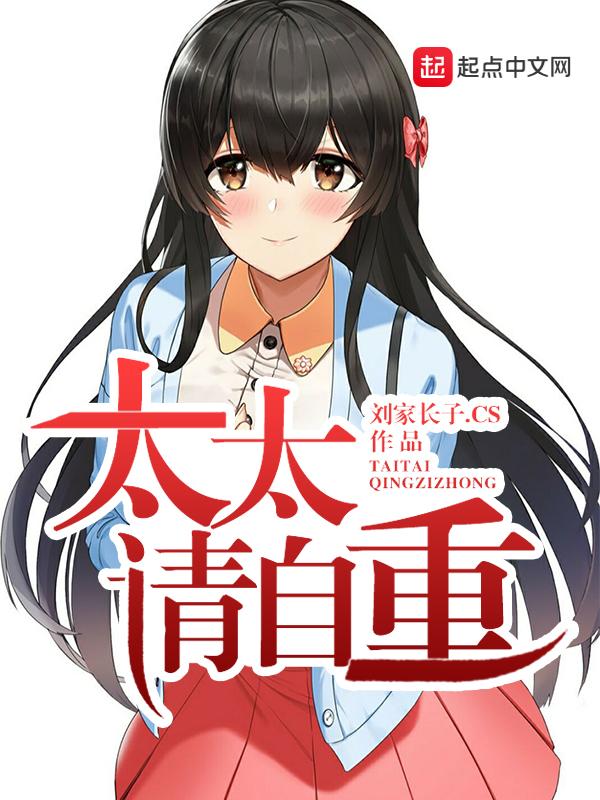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高武:陪练十年,一招出手天下知 > 第二百二十四章 这剑有点眼熟(第2页)
第二百二十四章 这剑有点眼熟(第2页)
东海市,赵擎拄着拐杖来到纪念馆外。十年过去了,他的腿再也无法恢复如初,但他每天仍坚持走完林北当年巡行的路线??从驿站到海边,来回七公里。
今天,他发现路边多了些变化。
原本杂乱的野草被整齐修剪,垃圾不见了,连墙上涂鸦也被一层薄薄的忆尘草覆盖,散发出幽幽蓝光。更奇怪的是,每隔五十米就立着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简短话语:
“这里曾有人扶起摔倒的孩子。”
“此处,一位母亲为陌生人遮伞。”
“这一角,清洁工老李扫了二十年。”
赵擎一路看下去,眼眶越来越热。他知道,这不是官方行为,也不是志愿者组织所为??这是普通人自发的纪念。
当他走到终点,面对那片新生的驿站荒地时,看见数百人已聚集在那里。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医生、教师、外卖员、程序员、渔民……每人手中都握着一把扫帚,样式各异,却都带着岁月磨砺的痕迹。
没有人说话。
他们只是默默排成队列,开始清扫这片尚未脏污的土地。
风起了,卷起些许尘土,又被下一排人轻轻扫净。动作整齐得如同训练多年,却又毫无预演的痕迹。这是一种本能,一种觉醒后的自觉。
赵擎站在人群之外,老泪纵横。他想喊些什么,却发现喉咙哽咽。最终,他放下拐杖,颤巍巍地从背包里取出一把旧竹扫帚??那是他十年前从林北宿舍拿走的遗物,一直供奉在家中的神龛旁。
他加入队伍,第一下扫地时,手抖得厉害。
第二下,稳了些。
第三下,耳边忽然响起熟悉的旋律??不是通过耳朵,而是直接从心脏升起。那是《归尘谣》,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清晰、完整,仿佛有十万个人在同一时刻哼唱。
与此同时,空间站内的王哲正漂浮在舷窗前,注视着地球。
“‘起点号’刚完成第10086次脉冲。”AI语音通报,“检测到全球共情场强提升至临界值。”
王哲点点头,轻声问:“它说了什么吗?”
“它说……该回家了。”
话音落下,那台由太阳能板与纳米纤维构成的巨大“星穹扫帚”突然调转方向,不再扫描大气层,而是将帚须对准地球表面,释放出一道前所未有的金色光束。这束光并未造成任何物理破坏,而是穿透云层,精准落在东海市那片新生驿站的中心。
石碑依旧无字,但在光芒照射下,碑面缓缓浮现出一行行名字??不是英雄名录,也不是贡献榜,而是十万零三千六百二十一个普通人的姓名,他们从未留名,却曾在某个清晨、某个雨夜、某条街角,默默弯腰,清扫了一片尘埃。
每一个名字浮现,对应的城市中便有一盏灯自动点亮,无论是否通电,无论是否有住户。那些废弃已久的房屋、倒塌的学校、荒废的车站,全都亮了起来,宛如星辰落地。
科学家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只能记录为“群体记忆具象化事件”。
***
同一时刻,苏念收到了第二封匿名邮件。
标题只有一个词:“回响”。
附件是一段视频。画面晃动,显然是手机拍摄。镜头对准一间老旧公寓的地板,一只手正在扫地。扫帚是普通的塑料柄,动作也不专业,甚至有些笨拙。但随着每一次挥动,地板缝隙中竟渗出点点蓝光,汇聚成一条细线,延伸至墙角。
那里,静静躺着一枚铜牌,表面布满锈迹,显然多年未曾使用。
忽然,一只手伸入画面,捡起铜牌,用力擦拭。锈迹剥落,露出底下清晰的刻痕:“林北?归尘者001”。
苏念呼吸一滞。
这不是伪造,也不是演绎。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场景,而且地点她再熟悉不过??那是林北生前最后居住的宿舍楼,早在三年前就被拆除重建。
可视频拍摄时间显示:**十分钟前**。
她猛地站起身,冲出教室,奔向海边卫星接收站。她需要确认信号来源,需要追踪这段影像的真实轨迹。
然而当她接入系统时,屏幕上跳出一行字:
>“不要找我,要成为我。”
紧接着,整个太平洋海底电缆网络传出一阵奇异波动。原本用于传输数据的光纤,此刻竟传导起一段音频信号??正是苏念上传的那句“我也在”。
这句话被放大、复制、重组,经由千万终端接力传播,最终汇入“回音”协议主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