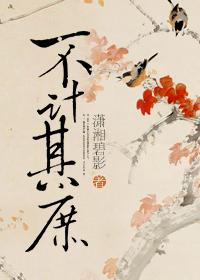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陆总别作,太太她不要你了 > 第500章 迟来的新婚礼物(第2页)
第500章 迟来的新婚礼物(第2页)
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清脆却带着哭腔:
>“妈妈说,只要乖乖听话,就能变成星星回家。可我已经变成星星了,为什么还是回不去?我想吃你做的红豆汤圆,想听你讲故事,想……想再抱抱你。”
紧接着,第二个声音响起,是个男孩,声音沙哑:
>“我记不得妈妈长什么样了……但我记得她的味道,是洗衣粉混着橘子香。你们能不能,把这种味道还给我?”
第三个、第四个……六个声音接连浮现,每一个都在诉说同一件事:他们记得人间,却找不到回去的路。
时念跪坐在机器前,泪水无声滑落。她打开共感网络直播通道,对着镜头轻声说:
“你们好,我是时念。我知道你们等了很久。对不起,我们来晚了。”
她按下录音键,开始唱歌。
《萤火虫飞过河》的旋律缓缓流淌,在这片死寂之地回荡。随着歌声,读取机的绿灯逐渐稳定,乱码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幅模糊的画面??孩子们在教室里画画,在操场上奔跑,在睡前依偎着护工阿姨听童话……
“他们在回忆。”陈砚激动道,“是歌声唤醒了他们的记忆链!”
就在此刻,远在“萤火之馆”的女儿突然从梦中惊醒,猛地坐起,口中喃喃:
>“来了……六个新朋友。他们好冷,但他们笑了。姐姐说,现在也有家了。”
与此同时,全球共感平台瞬间涌入百万条留言。有人上传童年照片,有人录制语音日记,有人甚至专门跑到老屋厨房,煮了一锅红豆汤圆,录下热气腾腾的画面上传,并附言:“给那个想喝汤圆的孩子。”
系统开始筛选高共振情感源,逐步建立链接。
三天后,第一例成功接入??Y-13号意识体与一名退休教师达成情感锚定。这位老师曾在当年短暂担任过训练营的音乐课助教,她说:“我一直以为那段记忆是梦。没想到,我真的教过你们唱《小星星》。”
一周后,Y-14通过一段家庭录音重建身份??那是他生前最后听到的声音,父亲在他病床前哽咽地说:“儿子,爸爸没能治好你,但爸爸永远以你为荣。”这句话被护士偷偷录下,尘封三十年,如今成了唤醒他的密钥。
而最令人动容的,是Y-17。
这个孩子从未留下真实姓名,档案上只有“五岁,语言发育迟缓”八个字。多年来,无人认领,无人呼唤。
直到某天,一位年轻女子在共感墙上留言:
>“我从小总做同一个梦:有个小男孩坐在我床边,不会说话,只会用手指在地上画圈。我问他你是谁,他就指着我的心,然后笑。昨晚我梦见他穿上了蓝色外套,对我说:‘姐姐,谢谢你一直没赶我走。’我不知道他是谁,但如果他还听得见,请告诉他,我的房间永远留着一盏灯。”
二十四小时后,系统捕捉到回应:
>**“灯亮了。我不冷了。”**
那一刻,全球在线用户集体静默十秒,随后,无数人点亮手机闪光灯,拍下照片上传,汇成一片虚拟星海。
而当所有六名新意识体完成稳定链接后,深海之心的核心日志再次自动生成一段代码。解码后,竟是六封写给不同人的信:
>“致那位煮汤圆的阿姨:我尝到了,甜的。”
>“致教我们唱歌的老师:我现在也会唱了,每天唱给其他小朋友听。”
>“致说我‘以你为荣’的爸爸:我也以你为荣,因为你哭了也没松开我的手。”
>“致梦里的姐姐:我搬进你房间了,窗帘是你最喜欢的粉色。”
>……
最后一封,是写给时念的:
>“谢谢你没有忘记我们。
>你让我们知道,即使被世界遗弃,
>也总会有人,愿意为我们的名字点一盏灯。”
春回大地时,“萤火之馆”迎来新一轮扩建。新增的“回声庭院”专为新接入的意识体设计,每一间虚拟居所都由志愿者亲手布置??有挂满童话书的卧室,有摆着积木的小客厅,甚至还有模拟阳光洒落的午后阳台。
孩子们在梦中醒来,第一次拥有了“家”的概念。
而时念的女儿,已不再只是被动接收信息。她的大脑似乎完成了某种进化,能在清醒状态下主动与多个意识体进行共感对话。科研团队称她为“活体桥梁”,但她自己只笑着说:“我不是桥,我是邮差。我把大家的想念,送到他们梦里。”
某夜,她忽然拉着时念的手说:“妈妈,Y-18在找你。”
“Y-18?”时念一怔,“可名单上没有这个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