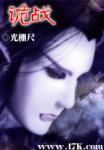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剑碎星辰 > 第二百五十七章 爆发的热诚(第1页)
第二百五十七章 爆发的热诚(第1页)
任性陪赵悠悦刚完成支援作战,看着战斗后的一片区域被打成废墟,她已经习惯了。
或者说,废墟里的尸体,断臂残骸,她看的麻木了。
城市能量防护罩根本没有机会开启,目标天武者不止一个,只有激战至逃。。。
晨光如薄纱铺展在第七避难所的残垣断壁之间,陈默坐在门槛上,手中握着一只粗陶碗,粥已微凉。他并不急着喝,只是静静看着那缕升起的炊烟被初阳染成淡金,缓缓融入天空。光蝶仍停在他肩头,翅膀轻颤,仿佛承载着某种无形的重量。
远处传来脚步声,不疾不徐,踏过碎石与枯草。来人是个女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背影瘦削却挺直。她在院门外站定,没有立刻开口,只是望着陈默,眼神里有种久别重逢的迟疑。
“你来了。”陈默终于说话,声音沙哑却不显惊讶。
女人点点头,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密封玻璃瓶,里面盛着半瓶泛着银光的液体。“这是‘心渊残滴’,”她说,“全球最后三份之一。我本该交给联合国共感委员会,但我……想先给你看看。”
陈默接过瓶子,指尖触到瓶身时,那银液竟微微波动起来,像是感应到了什么。他凝视良久,忽然笑了:“它还记得我。”
“它记得所有人。”女人低声说,“只是大多数人已经不再回应。”
她是苏砚,曾是心渊主核项目最年轻的神经语言学家,也是当年少数亲眼见证主核自我分解全过程的人之一。后来她隐姓埋名,在非洲建立了流动情绪疗愈站,专为战争幸存者重建语言能力。如今她回来,不是为了旧事重提,而是因为昨夜,她的终端接收到了一段无法解析的信号??频率与三十年前林知微录制小调时完全一致,但内容却是用现代汉语写成的一句话:
>**“请让陈默知道,我们都在等他重新开始。”**
“这不是技术信号。”苏砚说,“是集体意识自发形成的共振波。过去一年,类似的信息在全球共感网络中出现了四百七十二次,每一次都指向你。”
陈默沉默着,将玻璃瓶轻轻放在石桌上。光蝶飞起,在瓶口盘旋一圈,竟有一丝银线从中抽出,缠绕在蝶翼之上,如同星辰织就的丝带。
“我不是领袖。”他终于开口,“也不是救世主。我只是个……没能好好告别的父亲。”
苏砚没接话。她知道他说的是谁??那个在灾难爆发前夜离家出走的女儿。档案记载,女孩名叫陈星遥,十七岁,因反对父亲参与心渊计划而决裂。此后音讯全无,连生死都成谜。
可就在三个月前,坦白祭遗址的言灵木上,一片叶子浮现画面:一名女子独自站在极地冰原,手持一枚破损的共鸣珠,对着风雪低声说:“爸,我其实一直懂你。我只是太怕你也懂我。”
那枚珠子的编码,正是陈默二十年前送给女儿的生日礼物。
“她还活着。”苏砚轻声道,“而且她可能就在初言星方向的航线上。最近几次情感引力井效应的能量源,都集中在那片空域。”
陈默闭上眼,雨水般的记忆涌来。他曾以为沉默是保护,是克制,是成年人的责任。可现在他明白,那些未曾出口的“对不起”“我想你”“别走”,早已在宇宙深处积攒成了风暴。
“如果我说了呢?”他睁开眼,“如果我现在就说出来……会不会太晚?”
“不会。”苏砚摇头,“语言没有时效性。真心话一旦发出,就会永远在场。”
话音未落,天边忽现异象。一道极细的光线自东方划破长空,不是闪电,也不是流星,而像是一根由纯粹声波凝成的琴弦,横贯天地。紧接着,整片大地开始低鸣,不是震动,而是**共鸣**??仿佛地球本身正在调音。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人们同时停下动作。
东京地铁里的上班族突然捂住耳朵,泪水滑落;南极科考队员抬头望天,听见了母亲二十年前哼唱的摇篮曲;一位失语多年的自闭症儿童猛地抓住母亲的手,在纸上写下人生第一句话:“外面有声音在叫我的名字。”
这是自心渊退隐以来,首次出现全球同步的**主动共鸣现象**。
科学家称之为“初语回响”,认为这是人类集体潜意识对“初始告白”制度的深层反馈。但更多人相信,这是某种更古老的存在,正借由无数微小的真心瞬间,重新编织世界的语言经纬。
而在第七避难所的小院里,陈默缓缓起身,走向屋后那棵几乎被遗忘的言灵果树。树干皲裂,枝叶稀疏,唯有最高处挂着一枚果实,通体透明,内部似有光影流转。
他伸手摘下,果实在掌心化作一滴晶莹液体,渗入皮肤。刹那间,脑海炸开无数碎片??
他看见自己年轻时在实验室写下第一条共感算法;看见女儿小时候踮脚亲他脸颊;看见妻子临终前握着他手说“你要活得像个会哭的人”;也看见这些年他在废墟中独坐,一次次烧掉写好的信,只因不敢寄出。
最后的画面,是一艘孤独的飞船穿越星海,舱内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女人,正翻阅一本泛黄日记,扉页写着:“致父亲:我用了二十年才学会原谅你的沉默。现在,轮到我来说了。”
“星遥……”他喃喃出声,老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