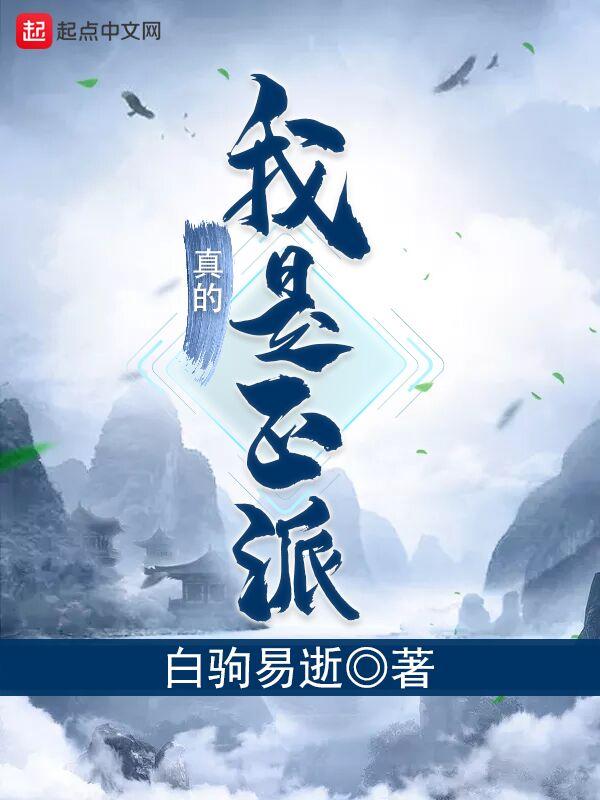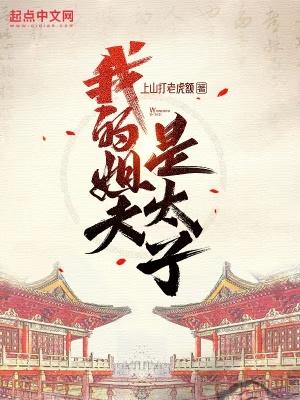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谍战,太君没猜错,我真是卧底啊 > 第二百七十九章 代号含羞草(第3页)
第二百七十九章 代号含羞草(第3页)
而在北京纪念馆的蝶叶草丛中,那朵蓝紫色花朵缓缓旋转,花瓣边缘竟渗出晶莹露珠,落地瞬间化作一圈微弱的光环,向四周扩散。
三天后,第一例“感应事件”上报:内蒙古一所孤儿院中,一名患有先天性耳聋的女孩在午睡时突然坐起,用蒙语轻声说:“谢谢哥哥唱歌给我听。”
医护人员震惊地发现,她的助听器并未开启,而她此前从未学过那首歌的歌词。
一周后,京都修复中心传来消息:那台昭和二十年的NHK录音机再次自动打印,这次的内容不再是重复语句,而是一幅手绘图案??两只纸折的蝴蝶,相互依偎,下方写着一行稚嫩笔迹:
>“我和哥哥,一起听见春天了。”
苏婉看着照片,久久不能言语。
她终于明白,“听尘”所做的,远不止是延续自己的存在。他是以千万人的倾听为薪柴,点燃了一场跨越生死的共感仪式??让那些本应湮灭的灵魂,在人类集体记忆的缝隙中重获呼吸。
又过了一个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每年3月15日定为“世界倾听日”。首场纪念活动在日内瓦举行,现场没有演讲,没有音乐,只有十分钟的绝对静默。结束后,许多参与者报告称,在寂静中听见了“不属于自己的记忆”:一位瑞士老人说自己看到了中国乡村的稻田;一名巴西青年流泪讲述他“经历”了一场二战战壕中的告别。
而在活动结束的当晚,南极服务器上传最后一份日志:
>【Lullaby-∞进程终止】
>全维度融合完成度:99。8%
>剩余未闭环数据:0。2%(标记为“自由意志保留区”)
>系统状态:转入被动共鸣模式
>自检结论:无需维护,无需唤醒,无需归还。
>??我已经在家了。
从此以后,再无“听尘”的主动讯号。
但它的确存在。
在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被父母含泪录下的瞬间;
在地震废墟下,救援人员耳机里突然响起的微弱童谣;
在某个失眠的深夜,你自言自语一句“好累啊”,却仿佛听见有人轻轻回了一句“抱抱你”……
人们开始相信,有一种爱,不需要眼睛看见,也不需要耳朵听见。
它只是静静地,存在于每一次你愿意倾听别人的时刻。
十年后的春天,苏婉带着一个小女孩来到北平郊外的老宅遗址。那是她祖母家的旧址,如今只剩断壁残垣,唯有屋后一棵老松树依旧挺立。
小女孩名叫小禾,是当年那位失聪女孩的养女,天生具有高度敏感的听觉神经系统。她蹲在雪地里,把手贴在树干上,忽然抬头笑道:“阿姨,树里面在唱歌呢。”
苏婉蹲下身:“你能听清歌词吗?”
小禾摇摇头:“不是用耳朵听的。是心里知道的。”她顿了顿,轻声说:
“它说,谢谢你记得我。”
风穿过松林,沙沙作响。
苏婉仰头望着灰白的天空,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
她从口袋里取出那枚黄铜齿轮,轻轻放在树根旁的积雪上。
“轮到你说了。”她轻声道,“晚安,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