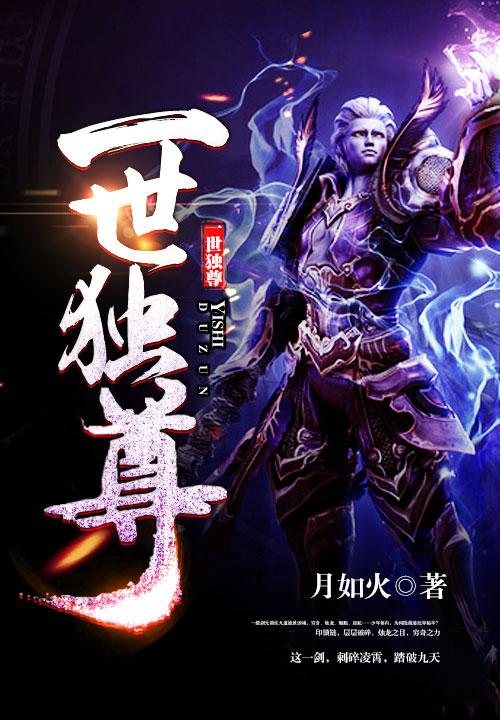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阵问长生 > 第175章 死仇(第2页)
第175章 死仇(第2页)
光桥剧烈摇晃,几欲崩塌。
千钧一发之际,记湖方向传来一声清越铃响。
不是来自烬余城的观忆台,而是直接响彻每个人的心底。随即,九州各地同时出现异象:东海石碑群齐齐发光,西北泉眼喷涌出带着文字的水柱,南陵遗址光幕再现墨言身影,她嘴唇未动,声音却传遍四方:
>“凡能感受痛楚者,皆有权守护记忆;
>凡愿说出真相者,即是守忆之人。”
刹那间,百万民众自发响应。
山村点燃篝火,老人开始讲述家族迁徙史;学童齐诵《勿忘铭》,声浪直冲云霄;工匠砸碎官府颁发的“标准史简”,换上民间整理的口述实录;甚至连边境戍卒也放下兵器,围坐一圈,轮流回忆家乡的模样。
这些声音汇聚成一股无形洪流,冲向那座摇摇欲坠的光桥。
桥身重新稳固,光芒愈发炽烈。而那股来自北方的压迫之力,在接触到这股集体意志后,竟如冰雪消融,瞬间溃散。
胜利并非靠武力赢得,而是靠记忆本身的力量。
此后十年,天下格局悄然改变。
朝廷被迫承认“多元史观”,设立“民忆司”,专管民间记忆采集与保护。各地兴建“忆馆”,不仅收藏文献,更配备共鸣阵法,可供访客短暂体验他人人生。一些极端派虽仍鼓吹“统一叙事”,但在一次次真实记忆的冲击下,其言论日渐式微。
最令人动容的变化发生在年青一代。
他们不再被动接受教科书上的“定论”,而是主动追问:“这是谁写的?为什么只写这些?有没有别的可能?”课堂上,老师讲述战争时,会有学生举手问:“敌军士兵的家人,后来怎么样了?”祭祖节上,少年不再只背诵祖先功绩,还会低声补充:“但他们也曾犯过错,我在这里替他们道歉。”
记忆,终于不再是负担,而成了成长的养分。
又是一个月圆之夜,记湖风平浪静,湖心亭中,陶罐依旧。
一位小女孩独自前来,抱着一本破旧的画册。她打开第一页,指着一幅歪歪扭扭的图画说:“奶奶说过,这是她小时候住的村子。后来打仗,全村人都没了。她说,如果没人记得,那个地方就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她顿了顿,轻声说道:“我现在记得了。我会讲给我的孩子听。”
话音落下,湖面微微一颤,陶罐口沿凝出一滴水珠,缓缓坠落。
那一瞬,整片湖水亮了起来,蓝光如潮水般扩散,照亮夜空。远方山岭间,观忆台上的铜铃无风自动,发出悠长清响。而在烬余城外的忆林深处,一棵新生的思木突然开花,花瓣飘落之处,地面浮现出一行行不断变幻的文字:
>我记得。
>我们记得。
>你们记得的地方,就是家。
风掠过大地,穿过村庄与城池,拂过碑林与学堂,最后停驻在那座无顶小亭之上。
一缕极淡的蓝光再次升腾,融入月色,无声无息,却贯穿古今。
它不属于任何人,又属于每一个人。
它不在高天,也不在幽冥,而在每一次哽咽后的诉说,在每一滴为往事流下的泪,在每一个决定不再遗忘的瞬间。
它只是存在着,像春天不肯融化的雪,像黑夜不肯熄灭的星,像人心深处那一声永不消散的低语:
>“我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