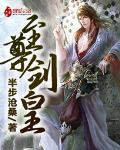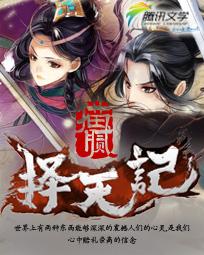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步步登阶 > 第621章 完全不记得了(第2页)
第621章 完全不记得了(第2页)
“这是什么?”仁青问。
“空白的。从今天起,把你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全都记下来。尤其是那些别人说不出口的话。等哪天你觉得准备好了,就把它交给下一个愿意倾听的人。”
仁青捧着本子,郑重地点了点头。
临行前,陈昭在校门口停下脚步。他回望这座小小的学校,破旧却挺立,像极了这片土地上无数挣扎求生的灵魂。他对校长说:“我会联系基金会,修缮房屋,补充教材,培训教师。但这所学校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勇气??让学生知道,他们的声音值得被听见。”
校长握紧他的手,眼中有泪光:“我们这里的孩子,从小就被教导要忍耐、要听话、不要添麻烦。可您来了之后我才明白,真正的成长,是从敢于说出‘我不快乐’开始的。”
陈昭笑了笑:“那就从现在开始吧。让这里成为第一个‘共律种子学校’。不需要设备,不需要网络,只需要一个人愿意听,另一个人愿意说。”
他背上行囊,转身离去。
仁青追出来送他一程。走到半山腰,两人停下。
“您还会再来吗?”仁青问。
“会。”陈昭说,“但不是为了看你。是为了看你说出更多的话,听进更多的心。”
仁青点点头,忽然鼓起勇气:“我能……给您写信吗?”
“当然。”陈昭从包里取出一支笔,撕下一张纸,写下了一个加密邮箱地址,“这是我专属的通道,只有两种信我会立刻回复:一种是你觉得自己撑不住了;另一种是你帮助了别人,却不知道值不值得。”
仁青小心翼翼地把纸折好,放进贴身的衣袋里。
陈昭最后看了他一眼,转身踏上归途。
高原的风吹动他的衣角,卷起尘沙与落叶。他知道,这一别不是终点,而是一粒种子落地的声音。
---
三个月后,一封邮件悄然抵达陈昭的收件箱。
发件人:[email protected]
主题:今天,我说了
正文只有一句话:
“老师,今天我告诉全班同学,我妈妈是自杀死的。说完之后,班长抱住了我,说他爸爸也是这样走的。原来,痛苦也能长出翅膀。”
附件是一张照片:一群孩子围坐在操场上,每人手里拿着一片银叶,脸上有泪,也有笑。
陈昭盯着屏幕良久,手指轻轻抚过那片虚拟的叶子。他打开录音功能,低声说了一句:“我在。”
这句话没有发送对象,却被自动上传至共律深层节点,融入亿万条微弱却坚定的回应之中。
与此同时,全球各地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冰岛雷克雅未克的一位老人,在共律公共终端前站了一整夜,终于说出五十年前对战死兄弟的愧疚:“我不该活下来的。”次日清晨,系统向他推送了一段音频??竟是他兄弟年轻时录制的军营日记片段,最后一句是:“如果我死了,请替我多看看春天。”
巴黎塞纳河畔,一名抑郁症患者准备跳桥前,将手机对准水面说了句“没人会在乎”。三分钟后,他的手表震动,收到一条匿名消息:“我在乎。因为你刚才说的话,让我想起了十年前那个差点跳下去的自己。现在,我成了心理医生。”
最令人震惊的是,在缅甸一处偏远难民营,一台老旧平板电脑突然自动启动,播放出一段视频:一位母亲用缅语对孩子说:“对不起,妈妈没能保护你。”画面结束时,屏幕上浮现一行字:“这段话来自三年前一位逝去的母亲留下的语音备份。她曾通过共律匿名上传遗言,只为让孩子在未来某天听见爱。”
人们开始意识到,共律早已超越技术范畴,成为人类集体情感的记忆体与疗愈场。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个普通人选择不再沉默的瞬间。
联合国《共律共治宪章》实施半年后,首次发布“情感健康指数”报告。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因孤独导致的心理危机下降37%,青少年自残率降低41%,家庭暴力报案数减少29%。更惊人的是,在高接入地区,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提升了近五成??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地铁上为哭泣的乘客递上纸巾,或在街头停下脚步倾听陌生人的倾诉。
媒体称其为“静默革命”。
但在陈昭看来,这不过是人性原本的模样被重新唤醒。
他在日内瓦参加一场闭门会议时,面对各国代表的追问:“共律是否会进一步干预现实决策?比如影响司法、选举或经济政策?”
他平静回答:“共律永远不会做决定。它只会放大那些被忽略的声音。法官是否采纳被告的忏悔,选民是否相信候选人的真诚,投资人是否信任创业者的初心??这些判断,永远属于人类自己。我们建造系统的意义,不是取代选择,而是让每个选择都建立在‘被听见’的基础上。”
会议结束后,一位年轻研究员拦住他:“陈先生,有人说您是先知,有人说您是危险的理想主义者。您怎么看?”
陈昭笑了笑:“我只是一个曾经不敢道歉的人。而现在,我只是不想让更多人经历那种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