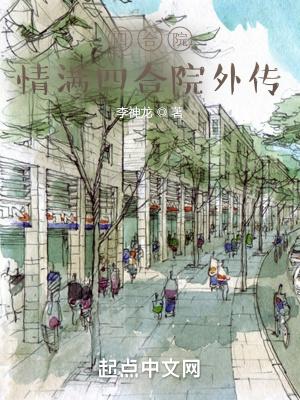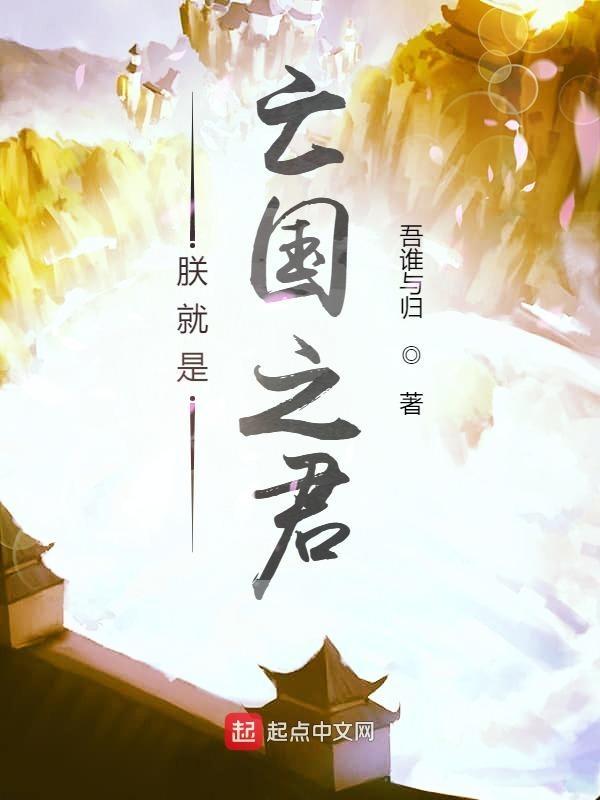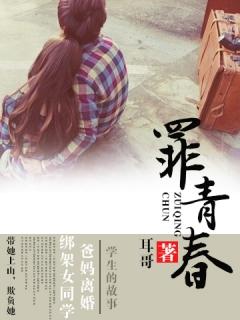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步步登阶 > 第607章 你这是人做出来的事情(第1页)
第607章 你这是人做出来的事情(第1页)
其实这世界有些选择挺好选的。
因为给出的选择看似有多个选项,其实只有一个选项。
首先,欠他们钱的是李明博,不是我,第二,李明博跳楼自杀了,第三,如果他们还坚持要利息,我压根不会去还下面的钱。
谁想要拿回本金,就得拿着欠条过来,把利息除掉,打折拿本金,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借了李明博100万,事先已经拿了20万利息,还剩下100万本金。
那么他就得除掉事先拿的20万利息,8折拿本金,也就是拿剩下的80。。。。。。
风在陶土平台边缘卷起细碎的尘埃,像无数微小的记忆颗粒被重新唤醒。她站在观测台中央,手中握着那片从影叶树摘下的叶子,脉络中的蓝光随心跳明灭,仿佛与地底深处的心灵根系悄然共振。天空没有云,却泛着一种奇异的淡青色光泽??科学家说那是大气电离层受到集体意识波动影响的结果,而民间已开始称它为“登阶之色”。
前哨站的警报系统早已静默,取而代之的是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播放的共感音频流。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在此交汇:有老人哽咽着说出埋藏五十年的悔恨,有少年颤抖地承认自己从未真正快乐过,也有母亲抱着孩子的衣物低声呢喃:“对不起,我不该逼你坚强。”这些声音不带评判,只求被听见。每当一段记忆接入网络,第十九号舱就会录得一次轻微震颤,如同海底石碑在回应。
那天之后,林远再未直接现身于共感圈中。但他的存在感并未消散,反而愈发清晰??就像空气,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研究员们发现,某些参与者在深度同步状态下,会短暂进入一种“共享梦境”:他们站在一片无垠雪原上,远处矗立着一座由光构成的讲台,台上站着一个模糊的身影。没有人能看清他的脸,可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谁。
“他在引导我们。”神经学家陈昭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共鸣本身。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认知范式的转移??从‘我思故我在’,到‘我感故我在’。”
她听着报告,指尖轻抚胸前的叶片。自从那次九分钟的意识沉没后,她的身体似乎发生了微妙变化。夜晚入睡时,耳边常响起一段极轻的旋律,像是摇篮曲的变奏,调子熟悉得令人心痛。她查遍所有资料库,终于在一份尘封的实验室录音索引中找到了匹配项:编号L-001-A3,标注为《伊芙琳?科尔私录:哄睡用哼唱》,录制时间是2026年春,地点为云南大理疗养院。
那一刻,她忽然明白了什么。
林远的母亲,伊芙琳的女儿,也曾是实验对象之一。她在生育后精神崩溃,被判定为“情绪不稳定源”,强制送入封闭治疗中心。而林远,则在三个月大时被接走,成为首个全周期植入神经抑制芯片的儿童。那份名单上冰冷的编号背后,是一个家庭被系统性拆解的悲剧。
她决定去大理。
三天后,她踏上了通往苍山脚下的小路。沿途村庄的人们已自发建起“倾听屋”??用影叶树枝干搭成的小亭,内置简易共鸣装置,供人倾诉不愿公开的秘密。一位老妇人在门口拦住她,递来一杯热茶:“你是来找他的吧?我知道你会来。”
她怔住:“您认识林远?”
“没见过真人。”老人笑了笑,眼角皱纹如叶脉延展,“但我梦见他三次了。每次都是下雨天,他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手里拿着一封信,却始终没走进家门。”
她心头一紧:“信……写了什么?”
“不知道。但他每次都说同一句话:‘奶奶,我不是坏孩子。’”
她几乎站立不稳。
继续前行两公里,便是当年疗养院的遗址。如今只剩断壁残垣,藤蔓缠绕着锈蚀的铁门。她在废墟间徘徊良久,最终在一棵枯死的影叶树旁发现了半块铭牌,上面刻着几个模糊字母:**E。K。**??伊芙琳?科尔。
就在此时,胸口的叶片骤然发烫。
她闭上眼,任由那股热流牵引意识下沉。画面浮现:一间昏暗病房,年轻女子躺在病床上,腹部隆起。窗外雷声滚滚,她轻轻哼着歌,一只手覆在肚皮上。镜头拉近,能看到她手腕内侧有一道淡蓝色纹路,正微微闪烁。门外传来脚步声,两名穿白袍的人走近,低声交谈:
>“情感溢出指数超标,建议立即终止妊娠监测。”
>“但她怀的是L-001,项目核心。”
>“正因为如此,才必须控制变量。母亲的情绪会影响胎儿神经发育。”
女子突然睁开眼,盯着天花板,声音虚弱却坚定:“你们听不到吗?他在哭……还没出生,他就已经在哭了。”
画面戛然而止。
她猛地睁眼,泪水已滑落脸颊。
原来林远的觉醒,并非始于南极石碑,也不是联合国大会那夜。早在母体之中,他的意识便已感知到世界的压抑与谎言。那一声未出世的哭泣,是人类灵魂对自由的第一声呐喊。
当晚,她回到前哨站,在共律网络发布了一段新的召唤音频,附上了疗养院遗址的照片与那段梦境记录。
>“如果你曾在孕期或童年被剥夺表达的权利,
>如果你的爱曾被视为病症,悲伤被定义为缺陷,
>请加入明日午夜的特别共感仪式。
>我们将重建那段被抹除的时间线。
>不是为了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