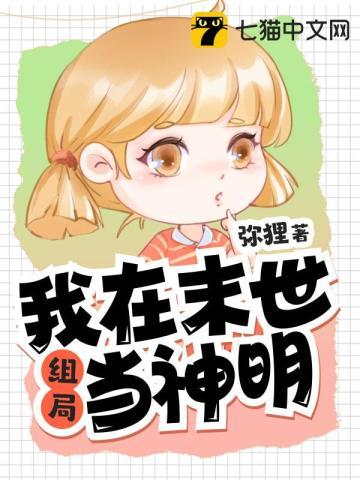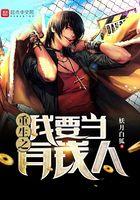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朱元璋的官,狗都不当 > 第二百一十一章 喜欢发明喜欢做研究(第1页)
第二百一十一章 喜欢发明喜欢做研究(第1页)
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
明州。
季风一到,所有即将出海的船只也是纷纷装货上船,准备扬帆起航。
倒是跟去日本的商船,时间上正好反过来。
日本的商船如今正是返航的时候。
一个。。。
雪落无声,却压弯了玄武湖畔的枯枝。朱允?立于亭中,目光穿破寒雾,落在远处城郭之上。那层层屋宇间炊烟袅袅,与天际低垂的云霭相融,仿佛一幅尚未干透的水墨长卷。陆明远欲言又止,终是轻声道:“陈默今日醒了一回,说想见陛下。”
朱允?缓缓点头,未动声色,只将手中梅帕收入袖中,转身踏上归途。
御医院内,药香浓郁,炭火微红。陈默卧于榻上,双目虽盲,神情却清明如水。听闻脚步声入室,他微微侧首,唇角牵起一丝极淡笑意:“陛下……脚步比三十年前稳了。”
“你倒还记得。”朱允?坐在床沿,声音低沉,“那时你在东宫伴读,总说我走路太急,像要赶着去赴死。”
“臣说的是‘心急则乱步’。”陈默轻咳两声,气息虚弱却不肯服软,“如今看来,陛下终于学会了等风来。”
两人沉默片刻,窗外雪粒敲打窗纸,如细语呢喃。
“朕已追复令尊官爵,赐谥‘忠宪’,配享太庙。”朱允?缓缓道,“你也该知道,这不只是为了你们方家,更是为了告诉天下人:忠不以成败论,义不在生死分。”
陈默嘴角微颤,良久才道:“家父若知此讯,必当含笑九泉。但他临终所愿,并非荣宠加身,而是希望后世之人不再因言获罪,因直遭戮。”
“所以朕设直言鼓,开《民意旬报》,建遗贤馆。”朱允?握紧他的手,“你说朕做得够了吗?”
“够不够,不在制度多寡,而在能否持之以恒。”陈默喘息稍定,继续说道,“陛下可还记得洪武末年,有位刑部主事因谏停海运被剥皮实草?当时满朝噤若寒蝉,唯有家父在私邸召集十三名同僚联名上书,结果如何?一人削籍,二人贬谪,其余皆罢官归田。从此十年无敢言者。”
朱允?闭目,喉头滚动:“朕记得。那封奏章,是你父亲亲手抄录给我看的。”
“今日虽许民言政,然人心畏权已久。百姓击鼓申冤,地方官仍可搪塞推诿;报纸刊载弊政,巡按未必敢查实惩办。制度若无铁律护航,终究只是纸上文章。”
朱允?睁开眼,目光如刃:“你想说什么?”
“请立‘监察御史直劾制’。”陈默一字一句道,“凡六科给事中、都察院御史,有权不经通政司转呈,直接面奏陛下弹劾三品以上大员。且规定:凡阻挠监察者,无论官职高低,一律革职查办,永不叙用。”
朱允?凝视着他,半晌不语。
陆明远站在门外,听得心惊肉跳。此举形同割裂文官体系的中枢权力,等于让监察系统凌驾于内阁与六部之上。一旦施行,必将引发朝堂地震。
然而朱允?只是轻轻点头:“准了。明日便下诏,命翰林拟旨。”
陈默脸上浮现出一丝欣慰,却又忽然问道:“陛下……当年宫火之夜,您真的一无所觉吗?”
空气骤然凝滞。
朱允?神色微变,手指微微收紧。
“什么意思?”他低声问。
“静闻师伯带回的青铜匣中,有一份未曾公开的密信。”陈默缓缓从枕下摸出一张折叠极小的黄绢,“是他临终前交给我的。信上说,那夜大火并非意外,而是有人故意纵火,目的不是杀您,而是逼您退位。”
朱允?呼吸一滞。
“写信的人是谁?”他声音冷了下来。
“信未署名,但笔迹与黄子澄先生极为相似。内容提到,先帝晚年已有禅位之意,曾密召礼部尚书郑沂起草传位诏书,却被燕王府细作截获。随后宫中内应趁夜纵火,制造混乱,迫使您仓促南逃。而真正的传位遗诏,至今下落不明。”
朱允?猛地站起身,来回踱步,脸色阴晴不定。
陆明远急忙进言:“陛下!此事若属实,则永乐继统本就非法!一旦公布,宗室必哗然,边镇或将生变,甚至动摇国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