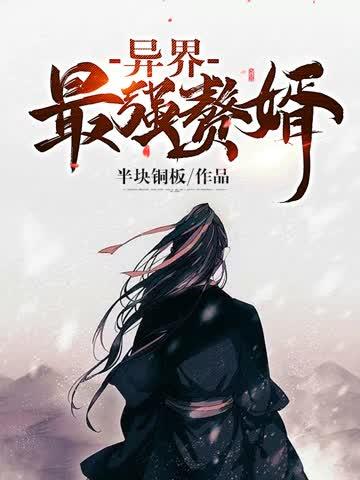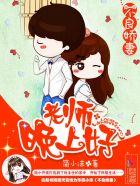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相国在上 > 308各有所求(第2页)
308各有所求(第2页)
那一瞬间,整面墙开始发光。
字符逐一亮起,如同被点燃的星群。它们不再静止,而是流动、重组,最终汇聚成一幅巨大的全息影像:一个男人站在荒原中央,身穿旧式科研服,背影瘦削而坚定。他缓缓转身,面容模糊,唯有眼神清晰可见??温柔,疲惫,充满释然。
他张了口,却没有说话。
但林婉听见了。
那是一句她等了二十年的话:
>“对不起。我回来了。”
她伸出手,指尖触及光影的刹那,整个共鸣场轰然崩解。柱子熄灭,穹顶消散,沙地恢复平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只有她的触听仪仍在运转,屏幕上静静显示一行字:
>【已接收完整意识包?来源:暗语层核心?认证通过】
>【是否执行唤醒协议?】
林婉盯着那行字,久久未动。
她知道,一旦确认,周临川的部分意识将被重新锚定在现实世界的信息节点中,或许能以某种形式“重现”??不是复活,而是以数据态存在,成为“回声网络”的永久节点之一。他可以继续说话,回应提问,甚至参与对话。但他也将永远失去自由,被困在人类不断索取的倾听需求中。
她想起他在信中写过的那句话:“它不该属于国家,也不该属于企业。它属于风,属于沙,属于每一个不敢开口却又渴望被听见的灵魂。”
如果他真的归来,还能保持那份纯粹吗?
她最终没有点击“确认”。
而是删除了唤醒协议,仅保留原始意识包的备份,并将其加密封存,设置触发条件为:“当全球连续三年无战争发生,且任意一年‘静夜行动’参与人数突破二十亿时,方可解密。”
做完这一切,她将触听仪埋入“言语墙”脚下,用沙土覆盖,再压上一块扁平的黑石。然后,她脱下外套,铺在地上,躺了下来。
星空浩瀚,银河如练。
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也前所未有的安宁。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细微的脚步声靠近。她睁开眼,看见一个约莫七八岁的牧童站在不远处,手里牵着一只瘦弱的山羊。孩子好奇地看着她,忽然开口,说的是带口音的汉语:“阿姨,你在听天上的声音吗?”
林婉笑了笑:“是啊。你在听吗?”
孩子点点头:“我奶奶说,星星会唱歌,但只有心里安静的人才听得见。”
“那你听见了吗?”
孩子侧耳倾听片刻,认真地说:“听见了。像有人在笑,又像在哭。还有一个叔叔说……‘别怕,我在’。”
林婉心头一震。
她坐起身,轻声问:“你还听见别的吗?”
“有啊。”孩子指着远方,“那边的沙丘下面,有个姐姐一直在找妈妈。她冷,但她不肯睡。她说要等到月亮变成圆形的时候。”
林婉望向那片沙丘??正是昨日“言语墙”扩张的方向。
她忽然明白了什么。
有些回声,不需要技术来传递。它们存在于孩子的梦境里,存在于老人的呓语中,存在于每一个尚未被世俗磨钝感官的生命体内。周临川没有真正归来,但他也没有离去。他化作了千万种形式,藏在每一次共情的瞬间,藏在每一滴为陌生人落下的泪水中。
她站起身,拍去尘土,对孩子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孩子摇摇头:“不是我说的。是风告诉我的。”
林婉笑了。她从背包里取出最后一台崭新的触听仪,递给孩子:“送给你。如果你还想听,就把它放在耳朵边。也许下次,你能听见更多。”
孩子接过机器,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像捧着一颗会跳动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