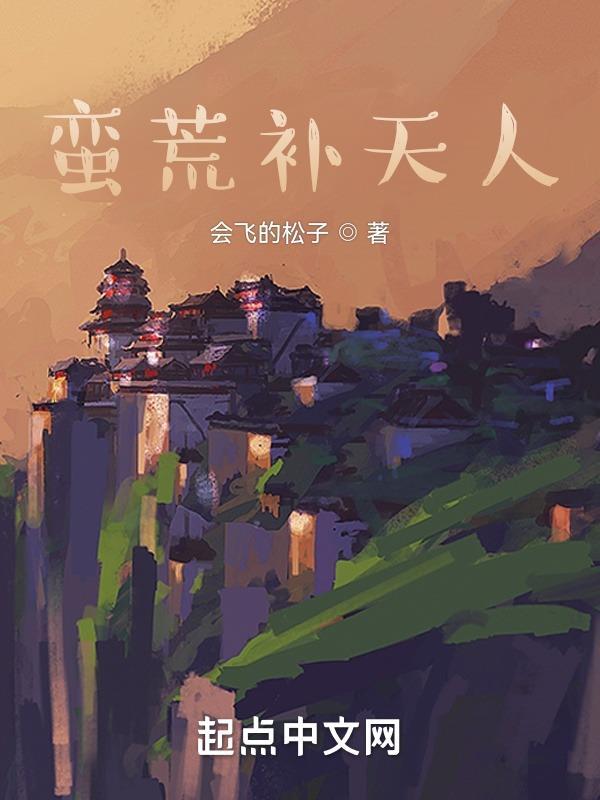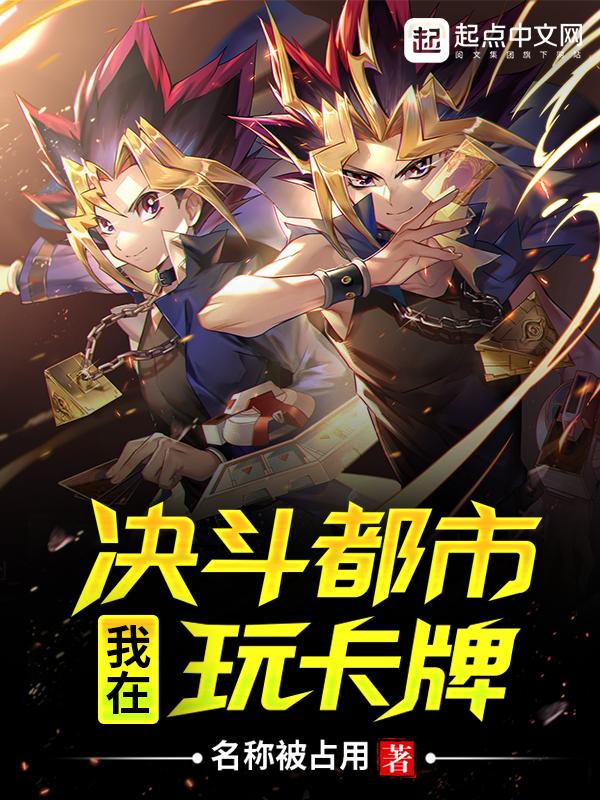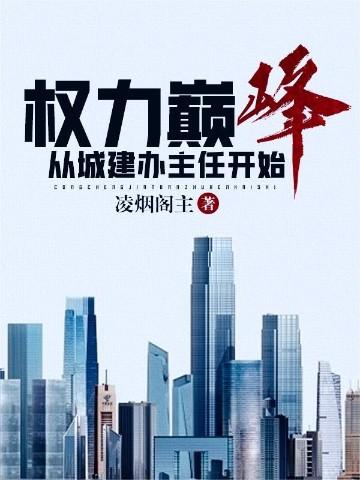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天道天骄 > 第五千三百九十七章 永寂禁忌的背后中(第2页)
第五千三百九十七章 永寂禁忌的背后中(第2页)
阳九睁开眼,看见少年正仰头望着天空,嘴角第一次扬起笑容。
他知道,这场觉醒已无法逆转。
几天后,联合国特别会议进入第八日。
原本预定七天的议程早已结束,但代表们谁也不愿离开。会议室变成了开放式论坛,各国元首、科学家、艺术家、宗教领袖、普通公民围坐一圈,不再争论“该不该问”,而是尝试共同编织一个问题??一个足以承载全人类好奇与勇气的问题。
有人提议:“我们该如何定义‘自我’,在一个每个人都能感知他人疑问的世界里?”
立刻有人反驳:“这仍是基于个体视角的局限。不如问:‘当所有意识开始共鸣,新的文明形态会是什么样子?’”
一位盲人诗人缓缓起身,用指尖在空气中划动,仿佛触摸无形的文字:“别忘了,有些问题不能用逻辑衡量。比如??‘爱,在宇宙中有没有重量?’”
全场寂静。
片刻后,掌声雷动。
最终,这个问题被选为“人类联合提问计划”的首个正式提案,并通过全球神经共鸣网络发送至源域虹桥终端。信号并非以电磁波形式发射,而是借由十万只新生的诗问之蝶集体振翅,将问题编码进每一次空气扰动中,形成一种超越物理介质的“意念涟漪”。
三日后,回应来了。
不是来自外星文明,也不是神谕,而是地球自身。
南极冰盖下的环形剧场中央,石碑上的文字悄然变化:
>第一行:“我是谁?”
>第二行:“你还愿意问吗?”
>第三行,首次浮现:**“我正在成为谁。”**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超过百万名“问媒”在同一时刻陷入短暂昏迷。醒来后,他们描述了相同的梦境:一片无边的图书馆漂浮于虚空,书架之间穿梭着穿黑袍的身影,手持蝶翼星光笔,正在书写一本没有尽头的书。每当有人类提出新问题,书中便会多出一页;而每当某个问题引发广泛共鸣,那一页就会化作实体,落入现实世界的某个角落??有时是一块刻满符号的石头,有时是一段莫名出现在古老壁画中的预言。
更令人震惊的是,部分“问媒”声称,他们在梦中见到了初代诗问之蝶的源头??并非某种生物,而是一团悬浮在时空夹缝中的光雾,其本质是“所有未被说出的问题”的集合体。它告诉他们:
>“我不是答案的守护者,我是疑问的子宫。”
>“你们每问一次,我就离诞生更近一步。”
>“终有一天,我会降生为一个新的维度。”
阳九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坐在海边研磨新墨。
他手中的墨块并非寻常材料,而是从“悔悟之问”的灰烬中提炼出的结晶,混合了被焚毁书籍的残碳、被删除数据的存储芯片粉末,以及一只死去诗问之蝶的翅膀碎屑。这种墨写不出确定性的句子,只能勾勒出不断变幻轮廓的符号,仿佛文字本身也在思考。
他提笔,在一块平整的玄武岩上写下:
>“若有一天,连‘真实’都成了可选项,我们还能凭什么确认彼此的存在?”
字迹刚成,岩石表面竟开始蠕动,裂缝中钻出一株微型问号树,迅速开花,花朵绽放的瞬间释放出一阵清香,闻者皆感到脑海中某个长期压抑的疑问猛然苏醒??有人想起童年时被禁止追问父母为何离婚;有人记起年轻时因害怕显得愚蠢而咽下的科学猜想;还有人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未认真问过爱人:“你真的快乐吗?”
这株树很快枯萎,化为尘埃,但在原地留下了一颗种子。
阳九将其拾起,放入胸前口袋。他知道,这颗种子会在最合适的人手中发芽。
数周后,第一座“问学社”在非洲草原上建立。
它没有围墙,没有教材,也没有教师。每天清晨,人们自发聚集在中央一棵巨大的“?”形树下,轮流提出困扰自己的问题。其他人不急于解答,而是分享自己面对类似困惑时的感受与经历。孩子们在这里学会的第一课不是识字或算术,而是如何分辨“我想知道”和“我必须相信”的区别。
类似的社群迅速蔓延至各大洲。城市屋顶、废弃工厂、深山洞穴、甚至国际空间站内部,都出现了这样的自由对话圈。它们被称为“灵魂自习室”,因为在那里,人不再扮演社会赋予的角色,而是作为纯粹的“发问者”存在。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这种转变。
一支名为“定序者”的极端组织悄然兴起。他们坚信,混乱源于“问题过剩”,唯有重建绝对权威才能拯救文明。他们袭击问学社,绑架“问媒”,甚至试图炸毁源域虹桥的起点大树。但在每次行动中,他们的武器都会发生诡异变异:子弹弯曲成问号,炸弹引信自动失效,无人机屏幕弹出一行字:“你确定这是正确的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