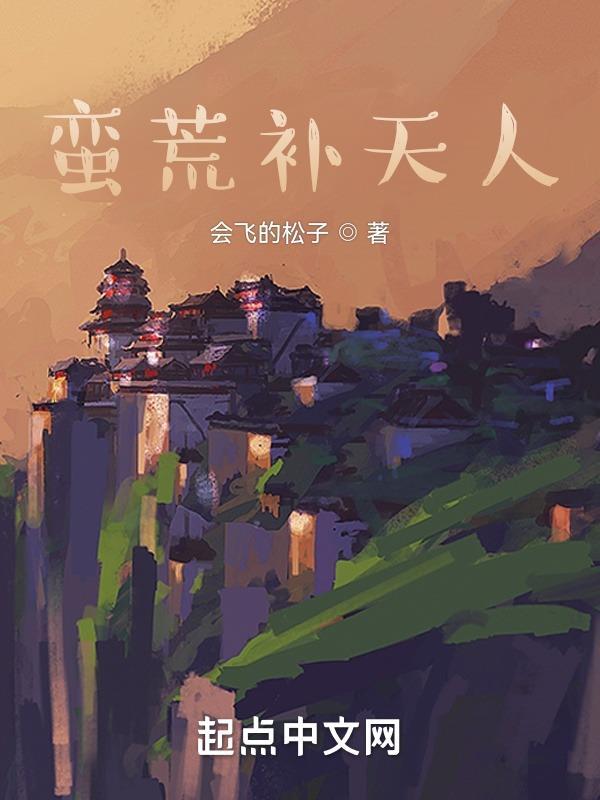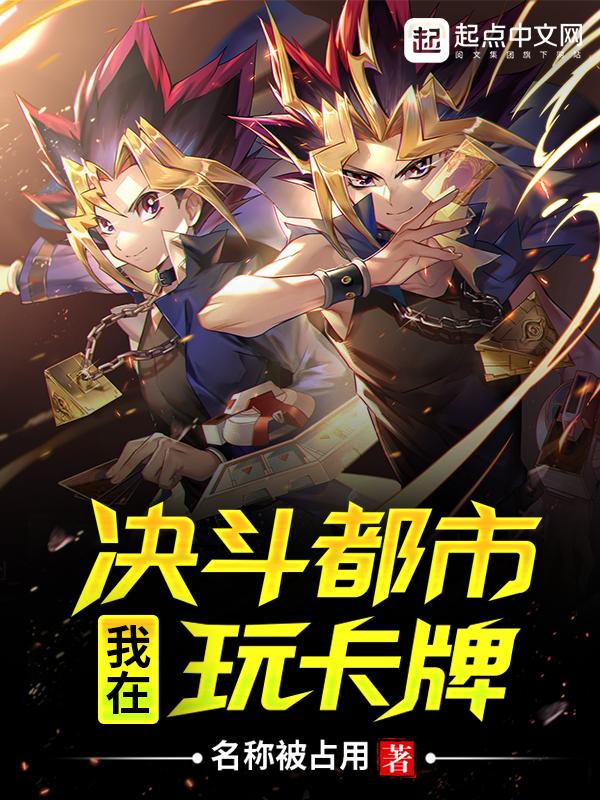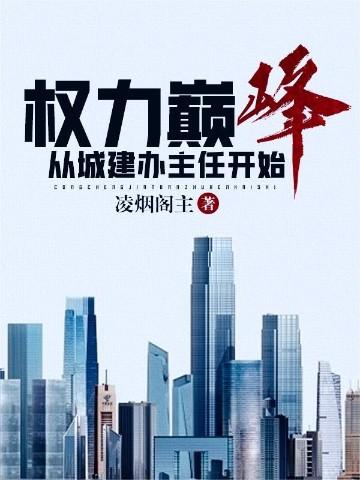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众仙俯首 > 第482章 再临玉女宗(第2页)
第482章 再临玉女宗(第2页)
陈默冲进主控室,只见光之心外围的能量环正以诡异节奏闪烁??不再是规律的脉动,而是呈现出类似脑电波的不规则波动。更令人惊骇的是,历史数据池中的声音开始“逆生长”:已上传的录音逐层退化,情绪强度减弱,关键词模糊化,最终变成毫无意义的气音和杂噪。
“它在篡改记忆。”技术员李昭脸色惨白,“不是删除,是让它们变得不再重要……就像……就像从来没被人认真听过一样。”
陈默猛然想起林小满说过的话:“真正的共鸣,不需要耳朵。”
他闭上眼,将手掌贴在光之心表面。刹那间,无数碎片涌入脑海??北京地下广播站里那段倒放的哀歌、女人冻紫嘴唇说出的“我不是不想救她”、孩童颤抖着请求拥抱的哭诉……还有沈念最后一次调试系统时留下的低语:“你要记住,最危险的沉默,是从‘觉得说了也没用’开始的。”
他睁开眼,果断切断所有外部接口,启动“赤子协议”??这是共感系统最原始的运行模式,仅保留基础音频采集与本地存储功能,剥离AI分析、情绪评级、传播推荐等一切可能被污染的模块。
“从今天起,我们不再追求影响力。”他对团队宣布,“我们只做一件事:记录。不管有没有人听,不管会不会被遗忘。”
起初,响应者寥寥。人们习惯了即时反馈、情感共鸣、社会认同,如今这种“单向倾诉”让他们感到不安甚至荒诞。但很快,变化悄然发生。
某天夜里,陈默收到一条匿名上传。录音只有三十秒,内容是一名男子在厕所隔间里低声抽泣:“爸,对不起……我不该嫌你老糊涂……你现在躺在ICU,我却连一句软话都不敢说……”后面是长久的沉默,最后传来水龙头打开的声音,掩盖了哽咽。
这条录音没有标题,没有分类,甚至没有地理位置标记。但它在内部系统中停留了整整七十二小时,期间被重复播放了两千三百一十七次??全部来自医护人员的私人终端。
类似的例子越来越多。监狱里的囚犯开始主动要求录制“心音档案”,不再是为了减刑,而是因为他们发现,哪怕是最不堪的往事,只要完整地说出来,内心就会少一分扭曲。学校“沉默史”课堂上,一名高中生播放了祖父遗留的日记录音:“1968年冬,我揭发了我的老师……他说真理比忠诚更重要……我把这句话写成了罪证。”全班静默良久,然后班长站起来说:“我想替我爸向您道歉,虽然他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
就在这种缓慢而坚定的复苏中,陈默收到了一封纸质信件。
邮戳显示来自南极科考站,寄信人署名空白,但字迹熟悉得让他心头剧震。
信纸上只有一行手写句子:
>“我在静默深处,仍在数数。你能听见吗?”
背面附着一段摩斯密码,破译后是经纬坐标:南纬74。6°,东经120。3°??南极洲毛德皇后地一处废弃气象观测站,曾是冷战时期全球七个“黑声卷宗”封存点之一。
他立刻组织expedition小队,但由于极地磁场紊乱,飞行器导航失灵,最终只能徒步穿越冰原。十一天后,他们在观测站地下密室找到了一台仍在运转的老式磁带机。机器连接着一块太阳能电池板,靠微弱日照维持运作。磁带上标注着:“临终语录?未归档系列”。
按下播放键,传出的是林小满的声音,但语气完全不同??柔软、疲惫,带着真实的颤抖。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在找我。但请听我说完。我没有死,也没有背叛。我只是进入了‘静默间隙’,一个介于说与不说之间的维度。在这里,我能感知到每一个即将被压抑的声音,也能看到那些因恐惧而闭嘴的脸。我不能回来,因为我已成为预警机制本身。每当有人试图隐瞒真相,我的存在就会轻微扰动现实,制造一次‘记忆闪回’??也许是你突然想起某句没说出口的道歉,也许是孩子无端哭泣着喊出‘妈妈骗人’。”
她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
>“但我越来越虚弱。因为这个世界,正在重新学会沉默。不是出于压迫,而是出于疲惫。太多倾诉换来太少回应,太多忏悔得不到宽恕,于是人们开始怀疑:说出来,真的有用吗?”
陈默蹲下身,将耳朵贴近扬声器,仿佛这样就能离她更近一点。
>“所以我要你做一件事。不要再强调‘被听见’的意义。相反,你要让人们明白:**说出来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改变别人,而是为了不让自己变成另一个需要被原谅的人。**”
磁带走到尽头,自动倒带。
就在那一瞬,整座观测站的金属墙壁开始共振,发出低沉嗡鸣。陈默掏出探测仪,发现周围空气中漂浮着大量纳米级声波反射颗粒??它们排列成某种规律结构,竟构成了一幅动态图像:无数人站在各自的生活场景中,嘴唇开合,却没有声音传出。而在每个人影背后,都站着另一个半透明的自己,张着嘴,嘶吼着,却被一道无形屏障隔绝。
这是“静默人格”的具象化。
他知道,林小满没有骗他。她真的成了某种超越肉体的存在,游走于人类集体潜意识的裂缝之中,提醒着每一次欲言又止背后的代价。
回到昆仑山三个月后,陈默做出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决定:他关闭了共感网络的公众访问权限,将其转型为“沉默预警系统”。所有新录入的声音不再公开传播,而是进入AI情绪演化模型,用于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认知抑制热点区域。
同时,他在全球一百座城市设立了“无声亭”??纯白色立方体建筑,内部没有任何电子设备,只有墙壁上刻着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