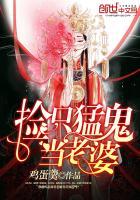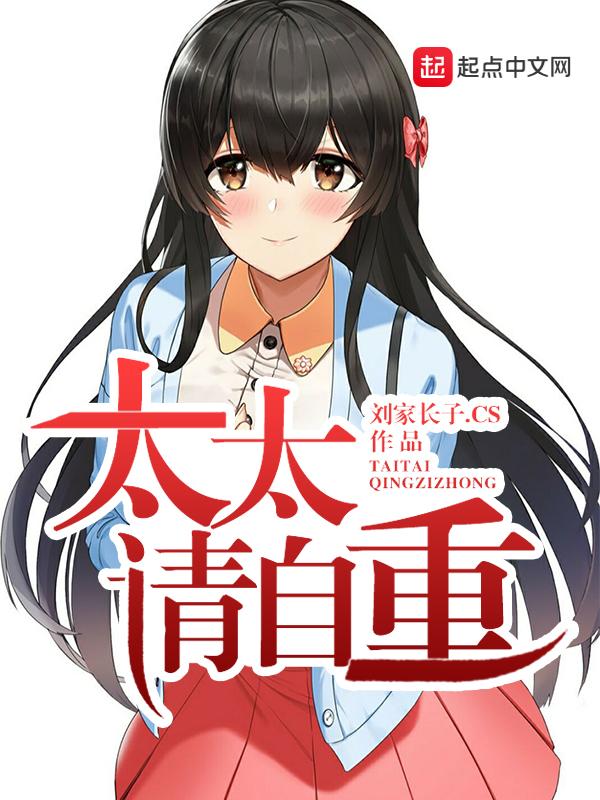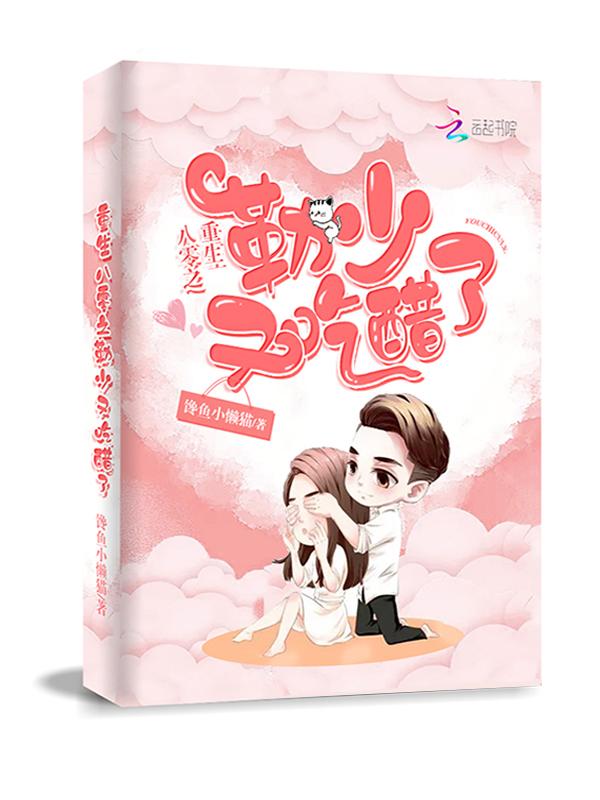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大明第一国舅 > 第685章 杀心渐重(第1页)
第685章 杀心渐重(第1页)
千叮咛万嘱咐好像也没多少效果,这小俩口实在太恩爱了。
朱元璋高兴,可是趁着马寻给常婉把脉的时候也说道,“老大又添了个儿子,你回头去看看,叫允?。”
马寻顿时一脸便秘,“怎么起这么个名字?”。。。
马寻一行人离开西安城已有三日,沿途风沙扑面,黄土漫天。三千精兵列阵而行,旌旗猎猎,甲胄铿锵,虽是护送亲眷,却也如临战备。汤和骑在马上,不时回头望一眼中军那辆朴素的青帷马车??那是邓氏与谢氏所乘,马寻则始终步行随行,说是“一路走来,也算养养筋骨”。可众人皆知,他胃疾未愈,每至夜深便隐隐作痛,只是从不声张。
第四日清晨,队伍行至绥德境内,忽有快马自北而来,尘烟滚滚,骑士披甲执令,高呼:“急报!西番十四族使者已入延安府境,声称奉秦王之命前来通好!”
汤和勒马停步,眉头一皱:“秦王前脚刚批准互市,后脚使者就到了?这般迅速,怕是有诈。”他转身看向马寻,“舅舅以为如何?”
马寻正倚着路边石墩歇息,闻言缓缓起身,接过军报细看片刻,眼神微凝。他沉吟道:“朱?性子倔强,但做事向来谨慎,不会贸然接见外族使节。若真是他下令放行,必有周密安排。不过……”他顿了顿,“十四族素来分散,彼此仇杀不断,如今竟能共推使者南下,倒是奇事。”
汤和冷笑:“莫不是有人暗中串联,借归附之名,探我关中虚实?”
“极有可能。”马寻点头,“传令下去,加快行程,务必在五日内抵达太原。另遣两队轻骑绕道北平,将此事密报朝廷,并通知叶升加强边境巡防。”
话音未落,忽听身后一阵骚动。只见邓氏掀开车帘,脸色苍白地唤道:“马寻!你快来!”
众人急忙围拢过去。原来谢氏昨夜受了风寒,今晨高热不退,额头滚烫,口中呓语不断,直呼“母后……静茹好怕……”。邓氏急得眼泪直流:“这可怎么办?再这样下去,怕是撑不到太原!”
马寻俯身探了探谢氏脉搏,眉头紧锁:“风邪入体,又兼心神郁结,若无良医调治,恐生变症。”他抬头问随军郎中:“药还有多少?”
“只够支撑两日。”郎中低声道。
汤和咬牙:“前方最近的州县是离石,距此尚有一百二十里,山路崎岖,若遇大雨,三日也未必能到。”
马寻沉默片刻,忽然道:“不能等了。我带十名亲卫,连夜赶路,先送谢氏去离石就医。你们继续前行,我会在途中与你们汇合。”
“不可!”汤和断然反对,“你是国舅,陛下亲授护卫之责,岂能轻涉险途?万一途中遭遇盗匪或敌探……”
“正因为我是国舅,才更不能看着亲人在我眼前倒下。”马寻语气坚定,“况且,我若不去,静茹的婚事也要耽搁。母后的遗愿,岂容儿戏?”
他说完,不再多言,亲自抱起谢氏登上一匹快马,翻身上鞍。邓氏含泪递上一件厚氅:“路上小心,别忘了吃药。”
“记着了。”马寻勉强一笑,扬鞭而去。
风沙之中,那一骑绝尘远去,背影孤决如刀刻。
***
与此同时,西安城内,朱?正端坐承运殿中,面前堆满了各地奏报。自马寻走后,他每日卯时即起,辰时上朝,午间批阅文书,傍晚巡视军营,夜里还要研读兵法、召见将领。短短数日,人已瘦了一圈,眼窝深陷,唇色发白。
叶升站在下首,神色凝重:“殿下,延安府传来消息,西番十四族使者团已进驻驿站,态度恭敬,献上牛羊百余头,声称愿年年纳贡,岁岁称臣。”
朱?冷笑:“纳贡?他们连文字都不通,何来‘称臣’之说?分明是试探。”
“正是。”叶升点头,“末将已命西安卫副指挥使李恪率五百精锐暗中监视,凡使者出入,皆有记录。目前尚未发现异动,但他们带来的随从多达三百余人,远超礼制所限,恐藏奸细。”
朱?沉思良久,提笔写下一道密令:“命李恪假扮商旅,混入其部,查清各族首领动向。另,派细作潜入陇右诸寨,查明此次联合归附,是否另有幕后主使。”
叶升领命欲退,朱?忽然叫住他:“信国公。”
“末将在。”
“我舅舅……可有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