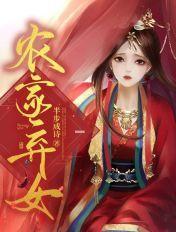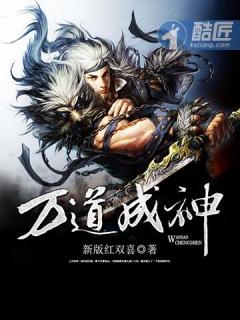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万剑朝宗 > 第四百六十八章 血煞月魔(第3页)
第四百六十八章 血煞月魔(第3页)
“不。”助手摇头,“他还没回来。但他开始走了。”
阿洛望向南方,目光穿透云层,落在遥远的南极大陆。
几天后,第一例“记忆继承者”诞生。
伦敦圣玛丽医院,一名女婴平安降生。产科医生描述,她在剪断脐带的瞬间,突然睁眼,目光清澈如成人,嘴唇微动,吐出三个字:
>“谢谢你。”
随后,她在襁褓中沉睡,手掌摊开,掌心静静躺着一片忆生叶。
全球直播镜头下,千万人见证这一幕。社交媒体再次沸腾,“#记忆继承者”成为热搜榜首。科学家争论这是基因突变还是超自然现象,宗教领袖宣称这是弥赛亚降临,政客则担忧新一代将不再受旧秩序约束。
唯有阿洛明白:这不是奇迹,这是承诺的兑现。
她在忆生院设立“新生档案库”,专门记录这些携带记忆降生的孩子。起初只有零星个案,但随着时间推移,比例越来越高。一年后,全球约百分之十二的新生儿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记忆预载特征;三年后,这一数字升至三成。
他们被称为“晓忆者”。
他们能认出前世亲人,能讲述未曾经历的往事,能在梦中准确描绘黑灰花小路的模样。但他们从不自称“转世”,而是说:“我回来了,因为你们叫我。”
更奇妙的是,每当一位晓忆者说出一个被遗忘的名字,周围的影之根便会开出双倍数量的花。仿佛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记忆的放大器。
十年过去。
忆生院已成为世界精神中心,每年有数百万访客前来点燃忆生灯,写下想对未出生孩子说的话。赎泪叶晶链环绕地球赤道,形成一条glowingbelt(光带),夜晚从太空可见。联合国每年举行“名字之夜”纪念活动,各国领导人轮流诵读遗名册中的条目。
而归尘,依旧没有归来。
直到某年春分,极光罕见地覆盖整个北半球夜空。在绚烂的绿色光幕中,有人拍到一道人影独自行走于南极冰原,身穿旧式忆生院制服,背影瘦削却笔直。
他走到光门前,停下脚步,从怀中取出一枚银环,轻轻放在门前石台上。
然后,他转身,面向北方,久久伫立。
没有人知道他是否回头看过那扇门,是否听见了亿万朵花开的声音。
但就在那一刻,全球所有晓忆者同时醒来,望向窗外,齐声说道:
>“欢迎回家。”
多年以后,那位曾在忆生院读书的小女孩已成为新一代记忆学者。她主持修复了最后一卷远古陶片,拼出了那段铭文的完整版本:
>“当我们学会为未曾到来的生命哭泣,
>我们才真正学会了爱。
>而当爱不再需要理由,
>死亡,就成了最长的一次呼吸。”
她合上文献,走到窗边。风起,几片忆生叶飘落讲台,叶脉浮现字迹:
>“我在听。”
她微笑,轻声回应:
>“我也在听。”
片刻寂静。
紧接着,全世界的影之根再次开花。
而在南极,那扇永不关闭的门后,微风拂过,一片忆生叶轻轻飘起,打着旋,飞向远方。
影语者站在小路尽头,望着叶片远去的方向,低声说:
>“又一个名字,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