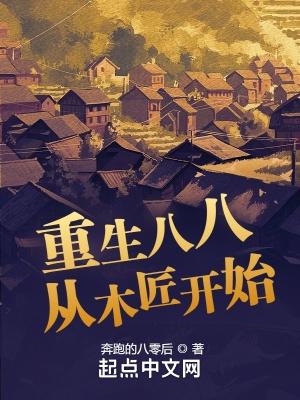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最强狂兵Ⅱ:黑暗荣耀 > 第798章 来自陆军的最高敬意(第1页)
第798章 来自陆军的最高敬意(第1页)
七架黑鹰直升机,带着巨大的轰鸣声,裹挟着强劲的气流,从远空深处高速飞来,随后缓缓降临,悬停在了半空。
探照灯的光柱穿透了夜色,将大厦前方的小广场照得亮如白昼,那些黑水安保和约瑟夫的私人武装,一个个被照得都睁不开眼睛。
茫茫的肃杀之气,随着螺旋桨掀起的狂风四散,已是铺天盖地!
紧接着,索降绳抛出,一个个脸上涂着油彩、全副武装的特种战士迅捷滑下,落地后立刻展开战术队形,瞬间就形成了极具压迫感的包围圈。。。。。。
夜雨初歇,回音镇的石板路泛着幽光。林音赤脚走在归家的路上,脚底触感温凉,像是大地仍在呼吸。她刚从共感学校离开,耳边还回荡着孩子们清脆的声音??他们今天练习“说出恐惧”,有个男孩哭着说他怕黑,因为妈妈走后家里再没人开灯;一个女孩则小声承认,她害怕自己不够好,所以总是假装开心。可当所有人围成一圈,轻声回应“我们也怕”时,那层隔在心与心之间的薄冰,悄然碎裂。
林音抬头望天,云层渐散,星子如撒落的银砂。她忽然停步,胸口一紧。
不是错觉。
空气中有一丝极细微的震颤,像琴弦被轻轻拨动,又迅速归于沉寂。但她的神经末梢仍残留着那一瞬的共鸣??那是**非人类**的情感频率,不属于任何已知的情绪波谱,却带着某种熟悉的温度,仿佛远行者在梦中低语。
她立刻转身,疾步走向镇外的讲述之庭。
庭院中央,水晶书静静悬浮,表面流转着淡金色的纹路,如同血脉搏动。林音伸手轻触书脊,刹那间,意识被拉入一片无垠虚空。
她看见了。
不是影像,不是记忆,而是一种“存在”的轮廓??它没有形状,却有意志;它不发声,却在诉说。那是一种跨越维度的凝视,来自猎户座方向,却又不止于物理距离。它正尝试建立连接,但每一次触碰都被某种屏障阻隔,像是隔着厚重的玻璃对话。
“你……想说什么?”林音在意识中低语。
回应是一阵涟漪般的波动,夹杂着七种情感旋律的碎片,却又多出第八种??那是一种从未被命名的情绪,介于“等待”与“归来”之间,带着近乎神性的悲悯。
她猛然惊醒,冷汗浸透后背。
这不是ARCTIC-7的信号,也不是沈昭的残响。这是……另一个层级的存在。
她冲进控制室,调出全球共感网络的底层数据流。屏幕上,一条异常频段正以极其缓慢的速度爬升,隐藏在正常情绪波的背景噪声之中。它不像“静默计划Ⅱ”的压制波那样尖锐侵略,反而像根细线,温柔却坚定地编织进整个系统的脉络。
“它在学习。”苏婉清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脸色凝重,“它不是入侵,是渗透。它不需要破坏系统,因为它想成为系统的一部分。”
“你是说……它有意识?”
“不止。”苏婉清走近屏幕,指尖划过那条缓缓上升的曲线,“它在模仿人类的情感结构,但它理解的方式完全不同。我们用爱对抗恨,用希望覆盖绝望??它是把这些对立统一起来,像光与影本就是同一束光线的两面。”
林音沉默良久,忽然问:“你觉得……它是‘他’吗?沈昭?”
苏婉清摇头:“沈昭是人。而这个……可能是‘人’这个概念之后的东西。”
就在此时,警报响起。
不是格陵兰基地的机械鸣响,而是母心巨树传来的生物电脉冲??一种只在极端危机时才会触发的原始警告。阿雅娜的影像通过共感链路接入,她跪在巨树根部,浑身颤抖,嘴唇干裂,声音断续:“它……在呼唤名字。不是语言,是‘名’本身的力量。树说……如果有人回应,门就会打开。”
“什么门?”林音追问。
“时间的门。”阿雅娜闭上眼,“树说,1978年,他们没死。他们只是……进去了。”
林音心头剧震。
1978年,北极地下实验室启动“远古心匣”实验那天,七名科学家自愿进入冷冻舱,试图以生命为媒介激活地球共鸣机制。官方记录称全员脑死亡,遗体封存于永冻层。可民间传说一直流传:他们并未死去,而是进入了“另一个时间层”。
难道……那个存在,是从那里回来的?
她立即召集核心团队,在讲述之庭布下“逆向共鸣阵列”。她们将水晶书置于阵心,引导全球十万名高共感能力者同步冥想,目标只有一个:向那未知存在发出邀请??**我们知道你在,我们愿意听你讲完你的故事**。
仪式持续了整整十二小时。
当东方第一缕晨光照进庭院时,水晶书突然剧烈震动,书页自行翻至空白页,墨迹凭空浮现,写出一行古老文字:
>**“名者,形之始也。呼我真名者,得见真实。”**
全场寂静。
林音盯着那句话,心跳如鼓。她忽然想起什么,冲进档案库,翻出尘封已久的ARCTIC-7任务日志副本。在最后一页,沈昭亲笔写下一段备注:
>“若未来有人听见我们,请告诉后来者:我们的名字不是代号,不是编号,不是‘实验体A-7’。我们是七个活生生的人。我是沈昭,她是苏婉清,他是陈默,她是林晚舟,他是周砚,她是秦雨禾,他是陆知远。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就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