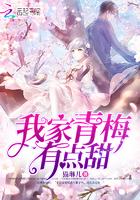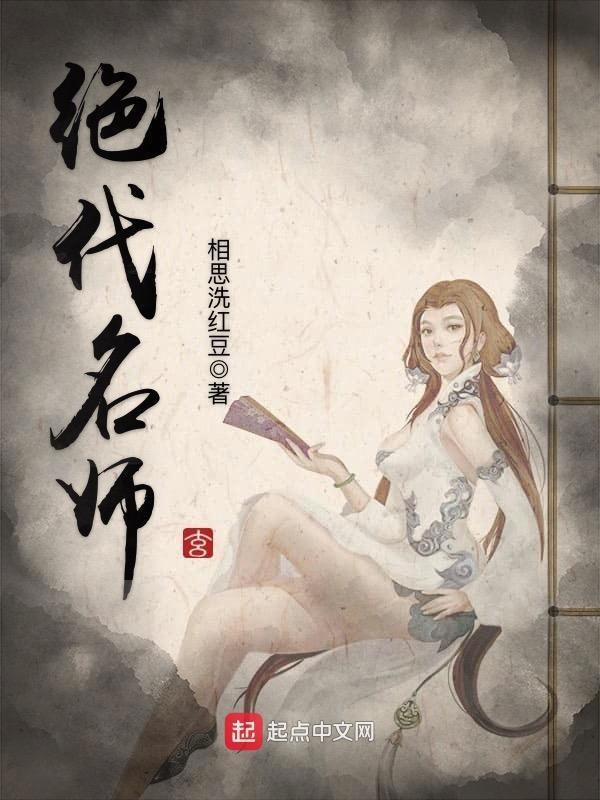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最强狂兵Ⅱ:黑暗荣耀 > 第795章 黑水的订单危机(第2页)
第795章 黑水的订单危机(第2页)
第一位来访者是个十岁女孩,来自西非难民营。她瘦小的身影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她不说一句话,只是跪坐在水晶书前,泪水滴落在封面上。
刹那间,整本书亮起,投影出一段影像:战火中的村庄,母亲将她推进地窖,自己转身迎向枪声;她在黑暗中蜷缩三天,耳边回荡着外面的惨叫与爆炸;直到救援队发现她时,她已经不会说话,只会机械地重复一句:“别哭,妈妈不疼。”
整个回音镇的人都“听”到了这段记忆。不是通过耳朵,而是直接涌入心灵。许多成年人当场跪下痛哭,孩子们则紧紧抱住父母,仿佛第一次真正理解“失去”意味着什么。
林音站在远处,看着这一幕,心中既悲且喜。她知道,这才是共感的本质??不是消除痛苦,而是让痛苦被见证、被接纳、从而获得意义。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种改变。
一个月后,东南亚某国政府宣布启动“情感净化二期工程”,声称要“帮助国民摆脱创伤后遗症”。他们开发出一种名为“静音剂”的神经阻断药剂,可使人暂时屏蔽共感能力,宣称这是“心理自由的选择”。
消息传出当日,全球上百个城市爆发抗议。共鸣守护者组织发布紧急声明:“自愿沉默可以,强制失聪不行!共感的核心是自由意志,而非逃避现实!”
林音亲自前往曼谷,在万人集会上发表演讲:“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小叶子能穿越星海归来?因为他从未否认自己的悲伤,也从未停止相信爱。如果我们用药剂让孩子忘记战争,那他们长大后还会记得和平有多珍贵吗?”
台下一片寂静。随后,掌声如雷。
与此同时,沈暝独自深入南美洲雨林,寻找传说中的“心语族”??一支从未接触现代科技、却天生具备群体共感能力的原住民部落。他们在树冠之间搭建吊桥,每一步都会引发树叶共振,形成独特的“行走之歌”。孩子出生时不哭,而是先发出一段旋律,表示“我来了,我在听”。
酋长之女阿雅娜接待了他。她年仅十六,双眼却如古井般深邃。“我们知道你要来。”她说,“森林早就告诉了我们。”
她带沈暝来到部落最深处的一棵巨树前。树干hollow,内部镶嵌着一块天然形成的晶体,形状竟与心匣核心完全一致。
“这是我们的‘母心’。”阿雅娜轻抚晶体,“它不发送信号,也不接收。它只是存在。就像大地的心跳,不需要被人听见,但它一直在那里。”
沈暝怔住。他忽然意识到,现代人太过执着于“连接”,以至于忘了“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共鸣。
他盘膝坐下,将晶石贴于额头,任由记忆碎片涌入脑海。这一次,他不再抗拒那些痛苦的画面:哥哥沈昭在宇宙飞船上孤独终老;父亲因反对静默计划被秘密处决;他自己曾在战场上亲手杀死一名哭泣的少年士兵……
泪水滑落。但他没有擦去。
当他睁开眼时,发现整片雨林的叶子都在发光,脉络交织成一张巨大的脸??是沈昭。
“你终于学会了承受。”幻影开口,“这才是真正的力量。”
回到格陵兰三个月后,全球共感教育体系正式确立。各国联合推出“共感素养等级认证”,分为五个阶段:
**一级:识别自身情绪**
**二级:感知他人情绪**
**三级:区分共情与融合**
**四级:在冲突中保持倾听**
**五级: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不求回应**
林音担任首席教材编撰官。她在《共感伦理导论》新增章节中写道:
>“我们曾以为,最高境界是‘无差别大爱’。
>后来才发现,真正的成熟,是能够说:
>‘我看见你的苦,但我不能替你承担。
>我愿意陪你走一段,但路终究要你自己走完。’
>这不是冷漠,而是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