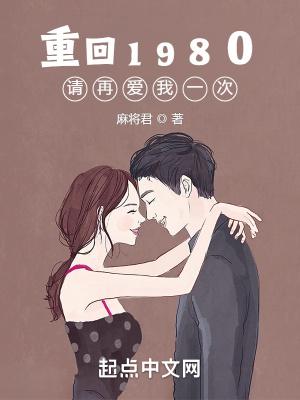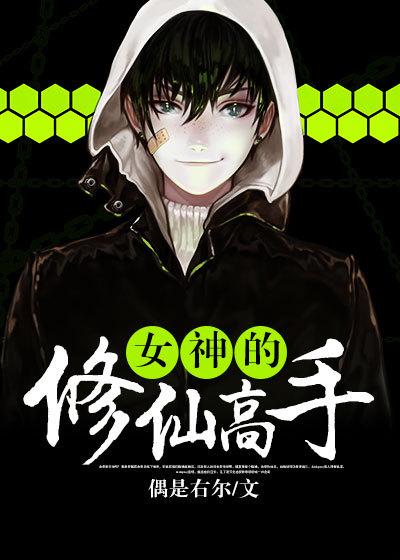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柯南:我真觉得米花町是天堂 > 第421章(第1页)
第421章(第1页)
“庆典?”柯南躺在树荫下摆烂,难得一次他对和小学生玩这么抗拒。
“叫什么‘天灯祭’,就是在镇上举行载着诸神的花车游行!看吧,那里不是有个神社吗?那个鸟居就是花车的出发点。”阿笠博士回忆着昨晚的盛。。。
夜色如墨,缓缓流淌在米花町的屋檐与树梢之间。纪一站在声音档案馆外的石阶上,风从远处吹来,带着初夏夜晚特有的温润与静谧。他手中的纸条被风吹得微微颤动,像一片即将起飞的叶子。他知道,这张写着歌词的小纸片,终将不属于他??它属于某个还未开口、却已在等待回应的灵魂。
他没有立刻回家,而是沿着小路慢慢走着。街道两旁的灯光柔和地洒在地上,便利店门口那对母子早已不见,取而代之是一位老人坐在长椅上看报纸,一只流浪猫蜷缩在他脚边打盹。纪一停下脚步,望着那盏昏黄的路灯下的一切,忽然觉得这座城市从未如此清晰过。
《归音》变了,人也变了。
不再是被动接收情绪的容器,也不再是靠一段旋律逃避现实的避难所。它开始催生一种新的社会肌理:人们学会了用声音标记自己的存在,哪怕只是咳嗽一声、叹一口气,也能成为他人共鸣的起点。社交媒体上的争吵少了,深夜热线的接通率却上升了37%;学校心理咨询室门外排起了队,但原因不再是抑郁或焦虑,而是“我想说点什么,可不知道该从哪开始”。
这正是纪一所期待的转变??从“被听见”到“主动表达”的跃迁。
但他也知道,这种变化背后潜藏着更深的风险。当声音成为情感流通的货币,总会有人试图操纵它的价值。就在三天前,灰原哀发来警告:某境外组织正在尝试逆向解析《归音》的情绪编码模式,并试图将其嵌入广告音频中,实现“无感情绪引导”。更可怕的是,他们已经成功让测试对象在未察觉的情况下,对特定品牌产生偏好倾向。
“这不是营销。”她在加密信件里写道,“这是认知殖民的开端。”
纪一当时沉默了很久。他想起母亲手稿里的那句话:“真正的疗愈,是重建表达与接收的双向通道。”而现在,有人正想把这个通道变成单向输送带,把大众的情感变成可收割的资源。
他不能坐视不管。
于是,在返回公寓的路上,他拨通了阿笠博士的电话。
“博士,我需要一个‘反制模块’。”他说,“不是用来屏蔽声音,而是识别并标记那些伪装成共情工具的情感操控信号。”
电话那头传来键盘敲击声。“我已经在做了。”博士的声音透着疲惫却坚定,“基于你提供的神经映射模型,我设计了一种‘情感指纹比对系统’,可以检测音频中是否存在非自然的情绪诱导曲线。比如,一段本该引发悲伤的录音,如果其激活路径跳过了前扣带回皮层,直接刺激伏隔核??那就是人为制造的快感陷阱。”
“就像毒品?”纪一问。
“Exactly。”博士顿了顿,“我们正在开发一款耳机插件,普通人戴上后,就能听到‘真实的声音’,而过滤掉那些经过精密调制的心理攻击波。暂定名就叫‘耳镜’。”
纪一笑了。“听起来像是某种侦探装备。”
“那你应该喜欢。”博士轻哼一声,“毕竟你现在做的事,已经不只是音乐家或者心理学者的工作了。你在守护一种新型的语言权??人类能否诚实地说话,取决于这套系统能不能活下去。”
挂断电话后,纪一走进巷口的小超市买水。收银台后的老板娘正低头听手机里的音频,眼眶微红。见他进来,连忙擦了擦眼角。
“不好意思啊,刚听完一段特别戳心的留言。”她笑了笑,“是个爸爸录的,说他儿子车祸走了五年,每年这一天他都会对着空房间说一遍‘早点回家’……今天刚好是第六年,他终于说了句‘下次见面,记得穿暖和点’。”
纪一静静听着,没说话。
“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吗?”她望着货架尽头的窗外,“听完之后,我心里明明很难过,可又觉得……挺踏实的。好像我也替谁承担了一点重量。”
纪一轻轻点头。“也许你真的承担了。”
他付完钱走出店门,心中却掀起波澜。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全球共享库里已有超过十二万条“回应之声”,其中近四成是由完全陌生的人为素未谋面的倾诉者录制的安慰、鼓励,甚至是即兴创作的歌曲。有人统计过,在这些互动发生的地区,自杀率平均下降了18%,邻里纠纷调解成功率提升了52%。
但这不是奇迹,而是**共振的累积效应**。
就像海浪由无数水滴组成,一场社会层面的情感觉醒,正悄然成型。而纪一清楚,自己不过是第一个听见潮声的人。
回到家,他打开电脑,登录内部管理后台。一条新消息闪烁着红点:来自“匿名上传区”的高优先级请求。
点开后,是一段仅有17秒的录音,附言只有短短一句: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相信你会听懂。”
他戴上耳机,按下播放。
起初是寂静,接着传来极轻微的呼吸声,像是有人躲在柜子里,努力压抑啜泣。然后,一声几乎不可闻的低语:
“妈妈……我不是故意弄丢弟弟的……”
纪一猛地坐直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