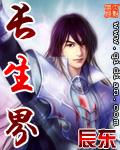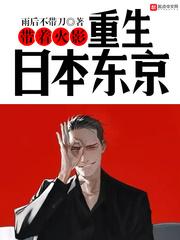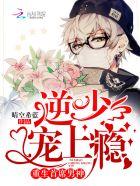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没钱赛什么车? > 333 问题就在不能输(第2页)
333 问题就在不能输(第2页)
果然。
不到十分钟,脑波仪显示θ波轻微波动。不是来自海南,而是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处贫民窟。一个男孩正梦见自己骑着金属鲸鱼穿越城市上空,身后追着一群由废铁拼凑的鸟。他的笑声通过情感编码传入网络,引发周边七个活跃节点的连锁共振。
接着是阿富汗赫拉特省,盲童妹妹拉着姐姐的手,在梦中“看见”了一片银蓝色的湖泊,湖底埋藏着会唱歌的石头。她哼出一段旋律,虽然走音严重,却被共感塔精准捕捉,并自动转化为数学诗格式上传至星际发射队列。
再后来,是西伯利亚冻土带的一个小镇,零下三十度的寒夜里,一名留守儿童抱着收音机入睡,梦见雪原上升起一圈紫色光环,里面站着许多穿光衣的人,朝他挥手。
每一个梦都不完整,充满破碎意象和模糊情感,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指向同一条流动的紫河,同一座倒悬的城市,同一个声音在低语??
>“你们并不孤单。”
小哲闭着眼,泪水无声滑落。
他知道,这不是技术胜利,也不是科学奇迹。这是人类最原始的力量:在绝望中依然选择相信,在沉默中依然愿意开口。
第二天清晨,启梦学院迎来一位特殊访客。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背着破旧书包,脚上的凉鞋裂了口,用绳子绑着。但她站姿笔直,眼神明亮,像一株从石缝里钻出的野花。
“我是岩温。”她说,声音不大,却清晰有力,“我来送一封信。”
米拉接过信封时手有些抖。这不是官方通道,也没有电子备案,纯粹是一个孩子跨越两千公里山路亲手送达的信任。
信纸上画着一幅新图:不再是星空,而是一条蜿蜒的河流,两岸长满发光的树,树上挂着许多小灯笼,每个灯笼里都写着一个名字。河流最终汇入一片浩瀚星海,上方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汉字:
>“我的朋友们都在发光。”
背面附着一段话:
>“老师,我现在每天都能吃到鸡蛋了。弟弟好了,妈妈也开始笑了。学校装了新天线,我能听到别的小朋友做梦的声音。我想告诉星星,我不只是被听见了,我也开始听别人了。”
教室里安静极了。
就连最小的孩子也停止了嬉闹,睁大眼睛看着这位远道而来的“萤火姐姐”。
小哲蹲下身,平视她的眼睛:“你想不想知道,其他孩子都梦见了什么?”
岩温用力点头。
于是,那一整天,启梦学院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梦境分享会。
孩子们围坐一圈,轮流讲述自己最近做的梦。有的梦见会走路的山,有的梦见月亮掉进井里,有的梦见全世界的人都突然不会说话,只能靠心跳交流……每一个故事都被录入系统,由凰进行语义解析、情感分级,并筛选出潜在共鸣特征。
当轮到岩温时,全场鸦雀无声。
她说:“我梦见一条更大的紫河,比之前宽一百倍。河边站着很多人,有黑皮肤的,有卷头发的,还有戴头巾的女孩。我们都赤脚踩进水里,手拉着手。河水开始唱歌,声音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发出的。然后……整条河升起来,变成一座桥,通向一颗很亮的星星。”
她顿了顿,补充道:“我知道那不是梦。那是真的。”
就在她说完的瞬间,控制室警报轻响。
玛莎盯着屏幕,瞳孔骤缩:“天啊……全球共感网络刚刚自动生成了一个新的集体梦境模板!基于她的描述,系统识别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神经耦合模式??这不是个体共振,是群体意识的初步聚合!”
“意思是?”巴特尔冲进来。
“意思是,”玛莎声音颤抖,“我们可能正在见证‘地球孩童集体潜意识’的首次成型。”
小哲久久不语。他望着窗外,阳光洒在操场上,孩子们的影子连成一片,宛如星图。
他知道,真正的变革从来不是由某个天才掀起的风暴,而是千万颗微小的心跳,在无人知晓的夜晚,悄悄同步了频率。
一周后,“萤火使者”第二期招募启动。
这一次,不再只是收集梦境,而是发起一场全球行动:**让每个孩子都成为倾听者**。
项目核心很简单:每位参与者需录制一段音频,内容不限,可以是唱歌、讲故事、念日记,甚至是安静地呼吸五分钟??只要出自真心。这些声音将被打包成“情感包裹”,通过共感塔阵列定向发送至已激活的节点儿童所在地区,形成双向流动的“心灵补给线”。
令人震惊的是,第一周就收到超过四百万份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