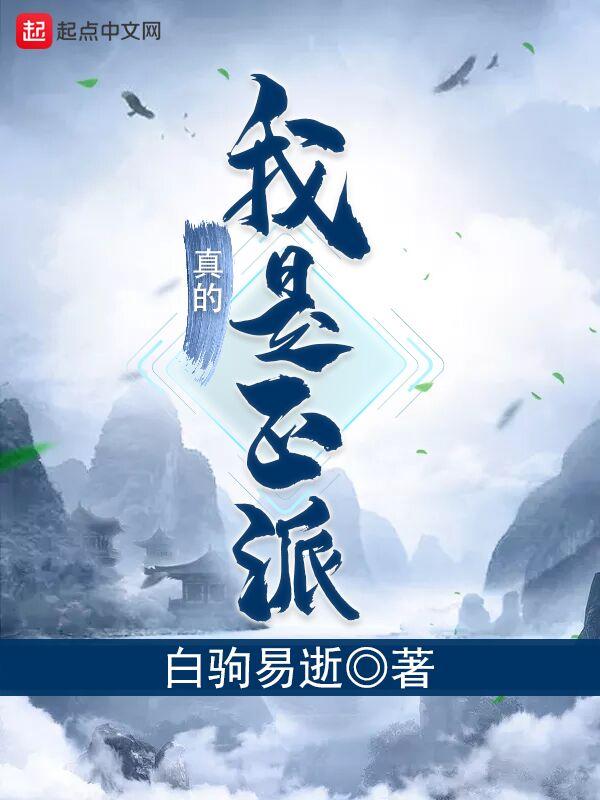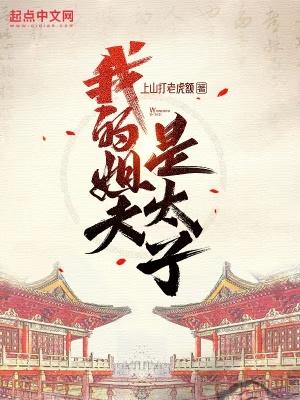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大宋文豪 > 第393章 没藏讹庞的应对(第1页)
第393章 没藏讹庞的应对(第1页)
夏国国都,兴庆府。
时值初夏,贺兰山麓的积雪早已消融殆尽,融雪汇成的溪流滋养着山脚下的草场,然而兴庆府内的气氛,却远不如这季节一般明朗温暖。
没藏讹庞的国相府虽也如汉地宫殿一般雕梁画栋、庭。。。
扎西次仁的信被打印出来,贴在文化园“回音墙”的最中央。那是一面由旧书页拼成的弧形墙面,每一封信都用牛皮纸信封装好,编号、归档,再轻轻嵌入缝隙之中。阳光斜照进来时,字迹仿佛浮在空中,像一群不肯落地的蝴蝶。
若兰每天清晨都会来这里走一圈。她不读全部,只随机抽出一两封,看孩子们写下的困惑与顿悟。有个甘肃的孩子说:“我把我妈骂我的话抄进《心光微课》的空白处,后来发现,那些话其实也在骗人??她说‘你不配’,可书里说‘你本就发光’。”云南一个傈僳族女孩写道:“我们寨子不让女娃上学,但我把U盘藏在猪草筐底下,晚上借着灶火听AI陆北顾讲‘人的尊严从何而来’。我现在偷偷教妹妹认字,她说等她长大了要当老师,专门收留逃婚的女孩。”
这些声音细碎如雨滴,却在地下汇成暗流。
春节过后,种子计划进入第二阶段。一百名青年联络人陆续提交了本地化方案。有人将《答门人问政十策》改编成川剧高腔,在茶馆演出时台下掌声雷动;内蒙古的牧民少年则把“萤火行动”谱成了长调民歌,马头琴声起处,歌词竟是“你问我为何还要相信远方?因为昨夜有信飞过戈壁,落在羊圈旁”。
而岩温也悄然变了模样。他不再沉默地坐在教室角落,而是主动组织“夜读会”,每晚九点,村小废弃的图书室便亮起一盏煤油灯。起初只有三五个同学来,后来连隔壁寨子的人都打着火把赶来。他们读的不是课本,是彼此写的信、摘录的句子、甚至是从广播里记下的片段语录。有人提议把这些内容编成一本“我们的书”,岩温点头,取名为《火塘边的话》。
他给若兰寄来一页手抄样本:
>“今夜讲的是‘怕’。阿爸说我若再念那些外来的书,就打断我的腿。可我还是来了。我不怕他打我,我怕的是将来我的孩子也得跪着听命令。所以我要记下来,哪怕只能传给一个人。”
若兰读完,当即拨通周维电话:“把这批材料整理出来,做成‘民间读本系列’,用傣文、彝文、藏文同步排版。封面不要印标题,就画一盏灯,或一支笔,让人第一眼看不出用途。”
周维低笑:“像当年的《共产党宣言》藏在菜篮子里那样?”
“比那更隐蔽。”她说,“我们要让思想穿上民俗的衣裳,唱着山歌走进千家万户。”
与此同时,官方的压力仍在升级。三月中旬,教育部通报批评五所高校“擅自引入未经审核的思想读物”,其中一所大学的图书馆竟收藏了三十七种不同版本的《全民共编版全集》,包括盲文版和手语视频光盘。校方解释称“用于比较研究”,但最终仍被迫公开道歉,并承诺全面清查。
然而讽刺的是,这份通报本身成了传播催化剂。网络上迅速出现名为《被禁的三十七本书》的清单,附带二维码链接至离线存储站点。更有程序员开发出一款名为“墨隐”的APP,用户只需拍摄任意一段文字,系统便会自动将其转化为看似普通的诗歌格式,实则内含加密信息。比如一句“春风拂面花自开”,解码后却是陆北顾关于言论自由的论述节选。
林舒从敦煌发来消息:陈守拙老人近日病情反复,但坚持完成了最后一段口述录音。题目叫《火种如何越冬》。
>“我在1957年烧过自己的笔记,一页一页扔进炉膛。火焰很高,灰烬很轻。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可十年后,我在劳改农场教一个放牛娃识字,他忽然问我:‘先生,你说“民为贵”是真的吗?’那一刻我知道,火没灭。它只是睡着了。
>思想的越冬之道,不在堡垒,而在人心深处那一丝不甘熄灭的微光。你要学会等待,像农夫等春雨,像母亲等孩子醒来。
>别怕沉默。沉默里藏着最多的声音。”
这段音频被拆分成十二段三十秒的小节,嵌入各地民间音乐平台的“禅意冥想合集”中。一位浙江听众留言:“本来想听着入睡,结果越听越清醒。这哪是冥想,这是敲钟。”
四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南方。暴雨连下七日,广西某县发生山体滑坡,冲毁了一所村级小学。救援队抵达时,发现教室倒塌的讲台下,压着一只铁皮盒。打开后,里面整齐码放着二十多封学生写给“萤火行动”的信,还有几张刮除墨层后显现批注的《遗稿补编》复印件。
最令人动容的,是一本湿透但仍可辨认的笔记本,扉页写着“岩罕的学习本”。里面记录着他逐字翻译《致后来者书》的过程,旁边密密麻麻标注着傣语发音。最后一页写着:
>“老师说这本书危险,不能看。可我看完了。我知道什么叫压迫,因为我们寨子的头人从来不让女人说话。我现在每天背一段,背熟了就去教妹妹。她说等她会写了,要把这些话刻在竹片上,挂在屋檐下,风吹过来,就能听见自由的声音。”
照片传到网上后,#铁盒里的信#登上热搜。央视虽未正面报道,但地方台悄悄播出一则五分钟短讯,题为《废墟中的课本》,镜头缓缓扫过那些泡胀泛黄的纸页,背景音乐是童声合唱的《萤火谣》。
若兰连夜赶往广西,在临时安置点找到了岩罕的家人。他的母亲抱着那只铁盒泣不成声:“他是好孩子啊……他说这些东西能救人……”
若兰蹲下身,握住那位妇女粗糙的手:“您的儿子已经在救人了。而且不止救一个人,他救的是未来。”
回到昆明后,她召集所有种子青年召开线上会议。画面中,有骑在马背上的蒙古族少女,有站在火塘边的彝族少年,有戴着头巾正在集市发纸条的维吾尔族修鞋匠孙子,还有西藏养老院里握着麦克风的扎西次仁。
“我们不能再依赖单一渠道。”她说,“从今天起,‘心光’不再是某个项目,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可以是一句谚语,一首儿歌,一次悄悄递出的纸条,也可以是你教会别人写下的第一个字。”
她宣布启动“百灯计划”:每位种子成员需在当地点亮至少一盏“隐形的灯”??可以是组织一次读书会,创办一份手抄报,或是仅仅坚持每天朗读一段文字给身边人听。
“不需要署名,不需要记录,只需要存在。”
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云南普洱一所乡村中学的语文老师发来一段视频。课堂上,学生们正齐声朗读一篇作文,题目是《如果我是陆北顾》。
>“我会躲在山洞里写字,写很多很多,然后让鸟叼着飞出去。人们捡到纸条,就会知道世界上还有人想着他们。我不怕被抓,因为我写的不是反诗,是真话。真话不怕见光,就像萤火不怕黑夜。”
声音清亮,穿透山谷。
与此同时,深圳“萤火车队”传来捷报:经过半年秘密筹备,他们在西南边境建成三条“文化走私通道”,利用跨境物流车、边贸商贩和返乡务工人员网络,将装有加密内容的微型设备送往缅甸、老挝华人聚居区。一名司机写道:“每次过境前,我都把U盘缝进坐垫夹层。没人查得出。我觉得自己像个地下党员。”
若兰没有回复,只是在日记本上写下:“当我们不得不成为秘密组织时,说明光明已成禁忌。但这并不可耻,因为守护火种的人,从来都不是靠旗帜行走的。”
五月,气温渐升,北方沙尘暴频发。北京某公园的“街头读书角”却被强制取缔。六位退休教师因在长椅上朗读《民本政经议》被带走问询。三天后释放,其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接受匿名采访时说:
>“他们问我为什么要读这些‘过时的东西’。我说,正因为它们被当成过时,才更要读。你们删掉了‘权力来自人民’,可历史不会忘。我们读,是为了提醒活着的人:你们曾经拥有过怎样的理想。”
这段录音通过蓝牙传输,在多个城市公园的音响设备中循环播放,伪装成“健康养生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