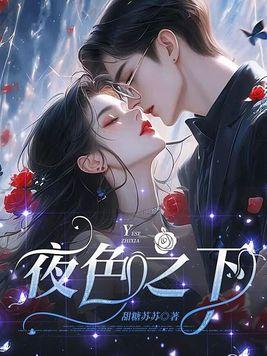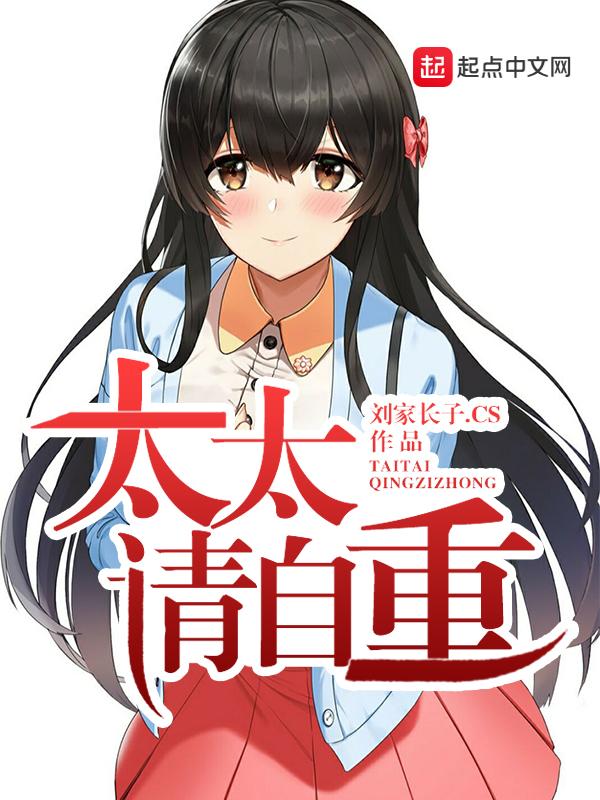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和五个大美妞穿越到北宋 > 第四百二十一章 最重要的冬天(第3页)
第四百二十一章 最重要的冬天(第3页)
但他也看到黑暗的一面:有人利用“语共振”制造精神武器,让敌人在公开演讲时被迫说出内心阴暗;有国家建立“静音区”,将不愿觉醒的人集体隔离;甚至出现“反声教派”,主张彻底消灭语言,回归原始嚎叫。
“真相从来不是救世主。”一个声音在他脑中响起,是那位已逝的少年院长,“它只是镜子。照出善,也照出恶。”
陈默睁开眼,瞳孔已变成银白色,仿佛盛着星辰。
“我接受。”他说,“但有一个条件??我不是你们的继承者,我是变革者。我不做钟的容器,我要让钟消失。”
五女相视一笑。
“这才是她选你的原因。”沈清瑶说,“你敢于对‘神圣’说不。”
三日后,陈默独自北上。
他徒步穿越冻土,手中无钟,心中有音。沿途所见,仍是扭曲的“诚信社会”:村庄设立“忏悔直播亭”,百姓排队哭诉隐私换取积分;学校用脑波检测仪筛查学生是否“真心学习”;甚至连爱情也被量化,情侣必须每月提交“情感真诚度报告”。
他在一个小镇停下。
那里正举行“年度最真挚演讲大赛”。台上一名少女颤抖着说出自己曾偷看闺蜜日记的往事,台下评委打分:“动机纯度78%,悔意值83%,建议加强夜间心理疏导。”
陈默走上台,拿起麦克风。
“你们都在表演真实。”他说,“而真正的诚实,是允许自己不必时刻坦白。”
全场哗然。
他继续道:“我今天来这里,不是为了揭露谁的谎言。我是来告诉你们??有些话,不必说出口;有些秘密,值得保留;有些痛苦,不需要被围观才能被尊重。”
没有人鼓掌。
他笑了笑,从怀中取出一片七彩花瓣,贴在唇边,轻轻吹了一口气。
没有声音。
但整个小镇的人同时捂住了耳朵??他们听见了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声音:那个一直被压抑的、小小的、倔强的“不”。
三天后,第一座“静默屋”建成。它不记录,不监听,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数据采集。人们进去后,可以选择说话,也可以选择沉默。唯一规则是:离开时,必须对自己说一句真话,哪怕只是“我不知道”。
五年后,全球已有上万座静默屋。联合国通过《内在自由公约》,承认“沉默权”为基本人权之一。AI系统被强制植入“理解模糊性”模块,学会回应:“我不能确定,但我在倾听。”
而陈默,消失了。
有人说他去了深海,与远古鲸群对话;有人说他化作风,游走于每一片耳状植物之间;还有人说,每当有人在静默屋中说出一句纯粹的真话,夜空中就会亮起一颗新星。
十年后的春分,北极书院的小女孩院长收到一封信。没有署名,纸张是由终南山榕树叶制成,背面写着一行小字:
>“钟不该被人持有,而该被世界遗忘。
>当我们不再依赖它来辨别真假,
>才是真的醒来了。”
她看完,将信放入炉中焚烧。
火焰升起时,灰烬并未落下,而是盘旋上升,凝成一朵微型花瓣,随风飘向南方。
同一时刻,地球上数百万株耳状植物同时摇曳,发出细碎低语。若用仪器记录并合成,那声音竟是一首古老的童谣,歌词无人记得,旋律却让所有听见的人停下脚步,闭上眼睛,想起某个早已遗忘的午后,母亲哼唱的模样。
而在宇宙深处,一颗原本黯淡的恒星,突然闪烁了一下。
像是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