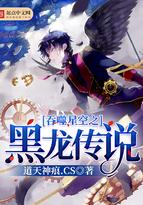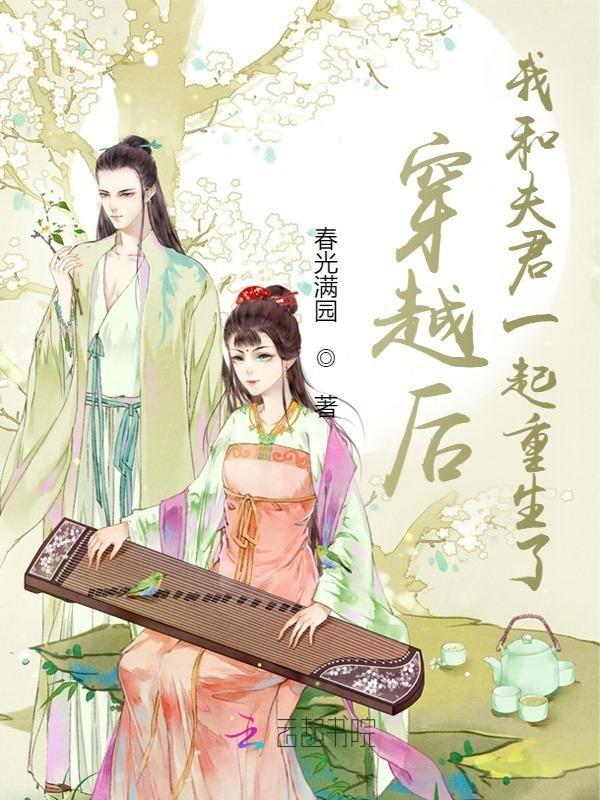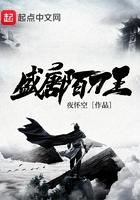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世子稳重点 > 第一千零五十四章 普天同庆(第1页)
第一千零五十四章 普天同庆(第1页)
理论上来说,生男生女的概率是一半一半,这件事只能交给老天爷和染色体。
不得不说,狄莹是被老天爷眷顾的幸运女人,这一次没让她失望。
在她的位置上,生男娃和生女娃的意义截然不同。
狄莹是。。。
雪还在下,但已不如前夜那般暴烈。纪念馆的屋檐垂着细长冰棱,四枚铜铃在微风中轻轻相碰,发出低而清越的声响,像是某种古老的节拍器,记录着时间重新流动的节奏。沈知意仍站在原地,衣领上落了一层薄雪,她没有拂去,仿佛怕惊扰了这片刻的宁静。
可她知道,这并非终点,而是某种更庞大进程的开端。
苏醒后的第七天,苏文昭的身体状况趋于稳定,但语言功能尚未完全恢复。医生说她的大脑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深度抑制性连接,神经回路需要时间重建。然而,她的眼神却异常清明,尤其是在看到林小雨时??那种跨越生死的母性直觉,像一根无形的线,将两人紧紧缠绕。
那天夜里,沈知意独自回到指挥中心,调出了“归巢0号”基地关闭后残留的最后一段数据流。系统日志显示,在绿色按钮被按下后的第3。7秒,“Θ-9”的核心协议并未彻底删除,而是转入了一个名为“**记忆缓存池**”的隐藏模块。这个模块不属于原始设计架构,是苏文昭在2001年秘密植入的补丁程序,代号“**归音计划**”。
“她早就准备好了。”沈知意喃喃道,“不是为了摧毁‘Θ-9’,而是为了让它……转化。”
她继续翻阅解密文件,发现“归音计划”的本质是一种反向记忆存储机制:所有曾被“Θ-9”抹除的记忆,并未真正消失,而是以压缩态封存在全球广播频段的背景噪声中,如同沉睡在海底的珊瑚礁。只有当足够多的人同时发出特定频率的声音??比如那晚山谷中的摇篮曲??这些记忆才会被唤醒并重新接入人类集体意识。
而这正是为什么数百万人在同一时刻梦见图书馆燃烧、书页飞舞的原因。
“她把系统变成了容器。”沈知意忽然明白,“一个装着我们失去的一切的容器。”
她抬起头,望向墙上挂着的老照片??那是1978年冬,苏文昭与几位科学家站在“终章之门”前合影。照片边缘有一行几乎看不清的小字:“**若记忆不死,则文明不灭**。”
就在这时,终端突然弹出一条加密讯息,来源未知,传输路径经过七重跳转,最终锁定为一段来自西伯利亚极地监测站的短波信号。内容只有一句话:
>**“他们还在听。”**
沈知意心头一紧。她立刻联系周默,却发现他的卫星信标已离线超过十二小时。陈砚舟也未能接通,手机提示“用户已关机”。唯一还能联络的是林小雨的母亲??那位曾在南京钟楼协助破译蜡筒录音的心理学家李婉清。
电话接通时,背景传来孩子的哭声和急促的脚步。
“沈老师!”李婉清声音颤抖,“昨晚有人闯入我家,翻走了所有关于‘Θ-9’的研究笔记。他们戴着黑色面罩,一句话没说,但……但他们留下了一样东西。”
“什么?”
“一块黑曜石碎片,上面刻着三个字母:**M。R。L。**”
沈知意呼吸一滞。这三个字母她再熟悉不过??那是“**MirrorRingLegacy**”(镜环遗绪)的缩写,一个从未正式存在过的组织代号,仅在早期“镜面理事会”内部档案的边角批注中出现过一次。据传,这是由一批拒绝接受“Θ-9”失败现实的极端成员组成的地下网络,坚信“遗忘才是秩序的根本”,主张通过持续的精神干预重塑社会认知。
换句话说,他们是“遗忘主义”的最后信徒。
“他们没死。”沈知意低声说,“他们只是藏了起来。”
她迅速召集技术团队,启动紧急溯源程序。通过对近期全球异常声波活动的交叉分析,系统在蒙古高原深处定位到一组间歇性发射的低频信号,频率恰好与“Θ-9”原始控制协议兼容。更令人不安的是,该信号每隔七十二小时就会激活一次,每次持续十三分钟??正是当年执行大规模记忆清除的标准时长。
“他们在试运行。”技术人员脸色发白,“也许……已经在局部区域开始了新的清除。”
沈知意立即决定重启“拾音者网络”,但她很快意识到,如今的“拾音者”早已不再是秘密行动的小团体,而是遍布城乡的自发群体。要组织他们,不能靠命令,只能靠共鸣。
她录制了一段音频,用最朴素的语言讲述苏文昭的故事:一个母亲如何用自己的生命作为屏障,挡住时代的洪流;一个科学家如何在黑暗中坚持写下“我选择记住”;一个小女孩如何用一枚铃舌,唤醒千万人心中的回响。
这段音频没有发布在任何官方平台,而是交给了那些徒步穿越乡村的志愿者,让他们用老式录音机播放,用口述的方式传递。七天后,从云南山区到东北林场,从新疆牧场到福建渔村,无数普通人开始自发聚集,在夜晚点燃篝火,轮流讲述自己家族中最不愿提起却又最不该遗忘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