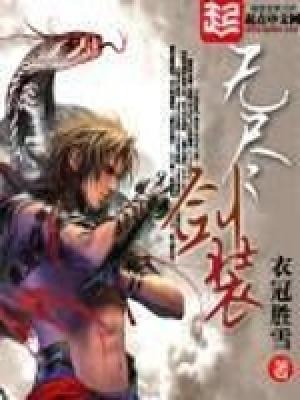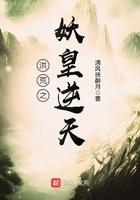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龙族:逼我重生,还要我屠龙 > 第473章 你妈也是家族指名的新娘(第3页)
第473章 你妈也是家族指名的新娘(第3页)
风波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直到某天凌晨,东京市中心的共感中枢突然自行启动,播放了一段长达十分钟的无声录像??画面中只有一个老人坐在窗边,看着雨滴落在玻璃上,慢慢滑落。没有配乐,没有字幕,甚至连镜头都没动过。
可数百万观众在观看后报告称,他们“听见”了某种东西。
有人说是童年母亲哼唱的摇篮曲,
有人说是初恋分手那天街角咖啡馆的钢琴声,
还有人说,那是他自己内心多年未曾察觉的叹息。
后来查明,这段视频是由一名双频教育体系毕业的少年上传的。他在说明栏写道:
>“这是我爷爷去世前最后一天。他不能说话了,医生说他已经失去意识。但我坐在这里,陪他看了整整一下午的雨。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感觉到我,
>但我知道,那一刻我们在一起。
>这就够了。”
这条视频迅速成为全球现象级内容,甚至被联合国收录进“人类情感遗产档案”。
三天后,《转型提案》获得国际议会联席会议通过。
与此同时,西伯利亚的树迎来了第十四次开花。
这一次,花瓣不再是纯白,而是泛着淡淡的虹彩光泽,如同油膜浮于水面。更令人震惊的是,每当有人踏入村庄方圆十里内,无论是否具备共感能力,都会在梦中见到同一幅场景:一片无垠的草原,七个人影背对着站立,面前是一道垂直悬浮的光幕,上面缓缓浮现七个名字??
那是她们生前从未公开的真实姓名。
科学家推测,这些名字可能是她们自我认同的最后一道锚点,如今终于愿意交付给世界。民间随即掀起一股命名潮,许多新生儿被取名为“曦”“予”“昭”“临”等源自七名静音者户籍档案中的单字。
而那个曾梦见前世的孩子,在花期开启当晚突然醒来,走到树前,伸手触碰一根低垂的枝条。
下一秒,整棵树剧烈震颤,所有花朵在同一瞬间绽放,又在同一瞬间凋零。
飘落的晶体并未随风而去,而是悬停在半空,组成一个巨大的环形符号??与我们在地核信号中发现的波形完全一致。
陈野拍下了全过程,并在通讯中问我:“你觉得……这是告别吗?”
我望着窗外正在降下的意识雪,轻声说:“不,这是签名。”
是的,签名。
她们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的底层代码里签下了名字。从此以后,每一次有人选择沉默,每一次有人尊重他人的孤独,每一次有人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都是在复写她们的存在。
三个月后,我在一次公开演讲中首次提出“多频共生文明”的操作定义:
>“所谓文明进步,不应以连接的密度衡量,而应以差异的容忍度为准绳。
>真正的共感,不是让所有人都发出同样的声音,
>而是让不同的声音都能安然存在,
>即使其中有一种,是沉默。”
台下掌声雷动。
但我注意到,前排一位戴着静音耳罩的老妇人没有鼓掌。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嘴角微扬,然后举起手中一杯清水,对着我轻轻点头。
我认出了她。
她是第一位接受“双频教育”的实验对象的母亲,也是当年在共感直播中目睹女儿猝死后陷入长期抑郁的受害者。如今,她已成为静默自治区最受欢迎的心理疏导师,专门帮助那些因过度共感而崩溃的人找回自我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