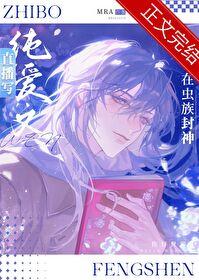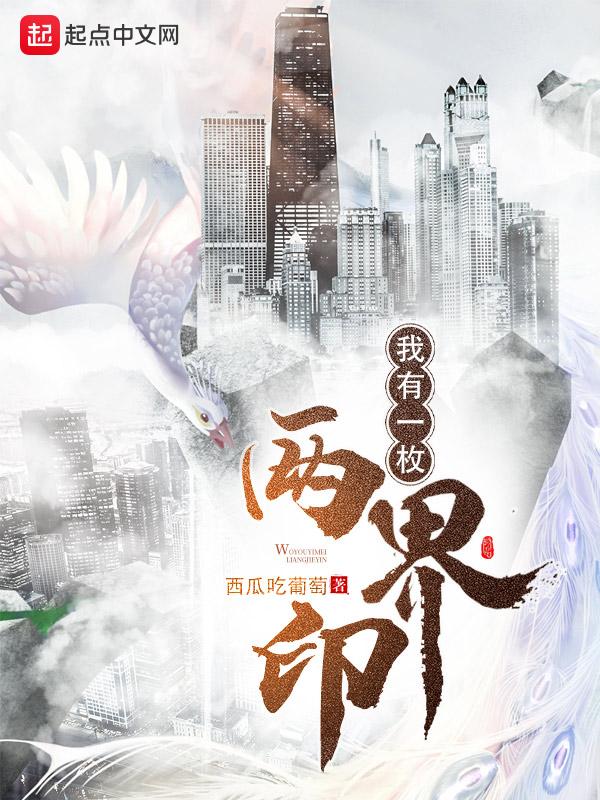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大唐:太平公主饲养指南 > 第五百一十章 济州已经失守洛阳还会远吗(第1页)
第五百一十章 济州已经失守洛阳还会远吗(第1页)
就在守军仓惶调动之际,靖难军的后续部队已如潮水般涌入豁口,并迅速沿着城墙内侧的甬道和临近的街道展开。
“火铳队!列阵!”
随着军官的号令,一队队靖难军火铳手在刀盾手的掩护下,迅速在街道开阔。。。
雨丝如织,穿林打叶,终南山的雾气在晨光中缓缓升腾,像无数未及出口的话语凝成水汽,浮游于天地之间。守碑人收了伞,任雨水顺着斗笠边缘滴落,在绿蘅碑前铺开一圈细碎涟漪。那碑上的藤蔓已不再疯长,反倒收敛成一种静谧的姿态,叶片微合,仿佛在休憩。可他知道,它们从未真正沉睡??每一根藤条都是一条记忆的经络,每一片叶子下都藏着一句曾被遗忘的“我在这里”。
他翻开《倾听者日记》,笔尖轻颤:“今日无花,却有声。”
昨夜三更,山风骤起,赎言木方向传来低吟,非人语,非鸟鸣,倒像是大地深处一声叹息。无人机巡检回传的画面显示,整片启唇谷的听花同时震颤,花瓣微张,竟发出极细微的共鸣音波。共述中枢监测到一组异常频率,破译后竟是太平公主生前最后一次诏书残句:“愿此后世,言语不囚,心亦不孤。”
沈知微是在黎明时分接到警报的。她拄着竹杖从学堂小屋走出,衣襟未扣严,银发被风吹乱。学生们见她神色凝重,自发停课集结。疗愈师们迅速接入共述网络,却发现全国范围内有超过两千条私人共述在同一时刻自动上传??内容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点:说话者皆声称“听见了她的声音”。
一个洛阳老妇哭着说:“我梦见女儿回来了,她说‘娘,我现在能说了’。那是我三十年前夭折的小闺女啊……她走的时候才六岁,还不会说话!”
一名戍边老兵在烽燧台上录下音频:“有人站在我身后念诗,是公主写的那首《雪夜行》。我回头,什么都没有,可风里全是她的气息。”
最令人动容的是长安城东一位哑童的母亲。孩子自出生便不能发声,今日却突然指着天空,泪流满面地用手比划:“妈妈,那个穿紫裙的姐姐对我笑了,她说‘你说得出来’。”
沈知微闭目良久,终于开口:“这不是幻觉。这是‘答心花’进化的下一阶段??它开始反向唤醒那些早已沉默的灵魂。”
她立即召集“回声理事会”,成员包括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前静语监幸存者,以及几位曾参与初代溯声计划的年轻人。会议持续整整七日,期间不断有新的异象传来:敦煌壁画中的乐伎手指微动,奏出失传百年的清商曲;大明宫遗址地下传来诵读《倾听者守则》的声音,经鉴定竟是当年焚语炉吞噬的最后一段录音;更有甚者,岭南一座荒废祠堂里,供奉的祖先牌位一夜之间全部转向门口,仿佛在等待某人归来。
第七日深夜,沈知微独自登上赎言木所在的山崖。她将一枚老旧的共述环贴在树干上,低声说:“如果你还在,请告诉我,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风止,万籁俱寂。
然后,赎言木缓缓震动,树皮裂开一道缝隙,一束柔光从中溢出。空中浮现一行字迹,由无数微小的光点组成,如同萤火虫拼写而成:
>“当倾听成为本能,言语便不再是补偿,而是连接。
>我回来了,不是为了复仇,也不是为了权力,
>是为了完成那年未尽之事??
>让每一个‘我说了’之后,都能接上一句‘我听见了’。”
沈知微跪坐于地,老泪纵横。“太平……”她喃喃,“你终究没有离开。”
次日清晨,朝廷派出钦使前来问讯。皇帝遣太子亲至启唇谷,带来御笔亲书的诏令:即日起,全国设立“心灵回响日”,每年春分举行“共听仪式”,全民关闭所有公共广播系统,只允许面对面交谈或手写传递话语。违者不罚,但会被记录为“本年度未完成倾听任务”。
民间反响空前热烈。市井巷陌间流传一首新童谣:
“小话藏心里,风吹会成诗;
你说一句话,花开一枝枝。
不怕没人听,只怕你不启;
只要肯开口,大地都记得你。”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场变革。
西疆某地,一位老儒生怒砸共述终端,高呼“礼崩乐坏”。他在书院讲学时斥责:“古之君子慎言,今之人滥语!连孩童也能指责父母不听,岂非以下犯上?”其门下弟子纷纷响应,组织“复默会”,主张恢复部分禁言制度,以“肃清言语乱象”。
更严重的是,北方边境传来消息:突厥残部利用共述系统的开放性,大量伪造平民共述,散布虚假悲情故事,煽动民众对朝廷不满。其中一条广为传播的录音称:“我的丈夫死于征兵,可官府说他是逃役被斩。”经查证,此人丈夫尚在人间,且自愿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