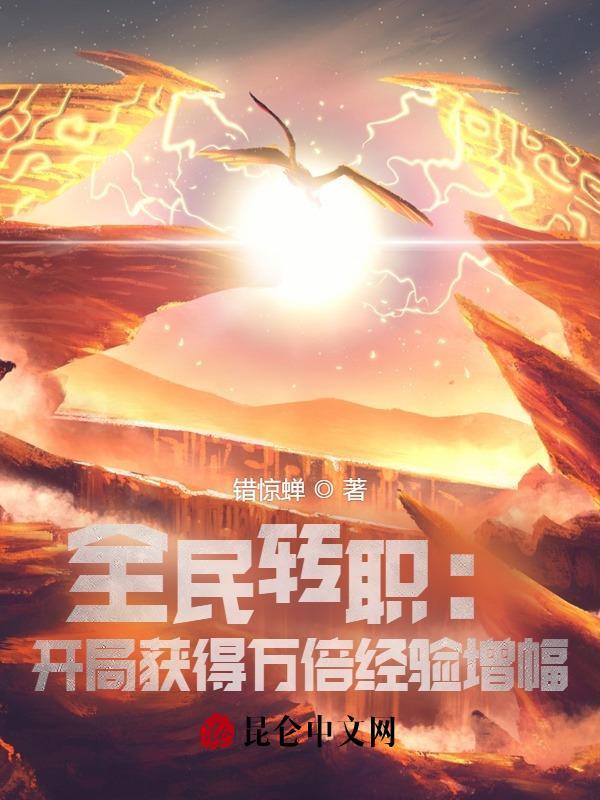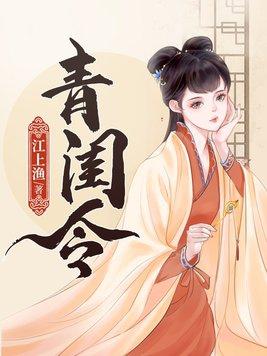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都重生了,我当然选富婆啦! > 第444章 关于家求订阅(第3页)
第444章 关于家求订阅(第3页)
吴丹则辞去研究所职务,成立“残声档案馆”,专门收集战争、灾难、监禁等极端环境下遗留的声音记忆。他常说:“历史不该只由胜利者书写。那些被抹去的声音,才是最该被保存的真相。”
这一年冬天,吕尧受邀参加日内瓦全球公益峰会。站在演讲台上,面对各国代表,他没有展示数据,也没有谈技术原理。
他只是播放了一段音频。
那是云南山村夜晚的合集:风吹竹林、溪水潺潺、狗吠、鸡鸣、老人咳嗽、孩子梦呓、母亲哼唱的童谣、父亲修理农具时金属碰撞的声响……最后,是一阵轻轻的脚步声走近,有人低声说:“我在。”
全场静默良久。
一位瑞典代表站起来鼓掌,泪水滑落。
会后,联合国秘书长私人助理找到他:“您知道吗?这段声音,将被刻入‘人类文明之声’金唱片,随下一代深空探测器发射至银河系边缘。”
“为什么选它?”吕尧问。
对方微笑:“因为它证明了一件事??在这个越来越喧嚣的世界里,仍有人懂得如何安静地倾听。”
回国途中,飞机穿越云层,舷窗外星辰密布。
吕尧靠在窗边,翻看手机里新收到的消息。
是那个曾回复“你好,年轻的我”的女孩发来的私信:
>“我报名了美术培训班。昨天画了一幅画,题目叫《听见光》。
>谢谢你做的这一切。
>我终于敢对自己说:我在。”
他笑了笑,回了一句:“欢迎回家。”
落地昆明,陈素芬已在出口等候。
“有个好消息。”她递过一封信,“‘倾听剧场’要全国巡演了。第一站,就是你老家县城。”
吕尧接过信,指尖触到一丝温热。
他知道,这场旅程远未结束。
真正的开始,或许才刚刚到来。
几天后,他重返故乡小学。孩子们正在排练新剧目《纸条》,讲述的就是阿坤与那位老师的故事。舞台上,一个小男孩跪在地上,用手语拼出“救救我”,而台下观众席中,每一位家长都被要求戴上耳机,聆听同步播放的真实录音。
演出结束,全体师生起立鼓掌。
校长握着他的手说:“以前我们总教孩子‘听话’。现在我们知道,更重要的是教他们‘倾听’。”
夜幕降临,吕尧再次爬上屋顶,打开音箱。
今晚播放的,是最新一期《百人合唱?无声之歌》??一百位曾经失语的人,用各自的方式“演唱”同一首旋律:喘息、敲击、手语节奏、心跳节拍、电子合成音……最终汇成一片浩瀚的声海。
风依旧温柔。
远处,又有几户人家亮起了灯。
他知道,有些人正按下录音键,准备说出埋藏多年的心事;有些人正戴着耳机,第一次感受到“被理解”的温度;还有些人,正因听到一句“我懂”,而决定重新拥抱这个世界。
他仰望着星空,轻声说:
“妈,你看,我们都学会了。”
“现在轮到我们,去听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