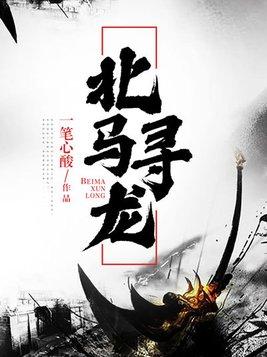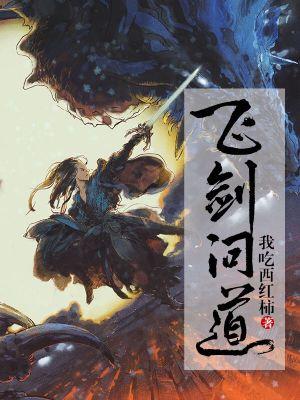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华娱从洪世贤开始 > 第677章出门在外男孩子要保护好自己(第3页)
第677章出门在外男孩子要保护好自己(第3页)
书页上,第四页开始浮现密密麻麻的名字,每一个都伴随着一段微弱的声波残留。那是无数普通人的声音??农夫、织女、士兵、学徒、母亲、流浪者……他们不曾留名史册,却构成了文明的根基。
全球范围内,又有超过五千万人经历记忆闪现。
北京胡同里,一位老太太突然用契丹语念完一首挽诗,惊呆全家;
悉尼海滩上,原住民少年捡起一根木棍,在沙地上画出祖先星图,精确对应今晚夜空;
莫斯科地铁站,一名乘客突然站起,用古教会斯拉夫语朗诵一段祷文,周围人群莫名跪下聆听……
政府再也无法封锁。
联合国正式成立“跨世记忆人权委员会”,首次承认“记忆传承权”为基本人权之一;国际法院受理多起文化遗产归还诉讼;ICPU在全球舆论压力下宣布解散,其高层成员陆续被捕。
但林浩然看不到这些。
在星海深处,战斗仍在继续。
缄默使徒并未退去,反而融合为一体,化作一口倒悬的巨钟,钟内全是蠕动的黑色文字,写着“禁止”、“销毁”、“不可知”等禁令。它缓缓逼近,意图将方舟彻底吞噬。
“最后一搏了。”林浩然深吸一口气,将书贴于心口,闭目回忆所有已读过的篇章。
然后,他开始吟唱。
不是某一文明的语言,而是十三种声音的融合??楚国史官的悲鸣、阿兹特兰鼓语的节奏、萨米鼓歌的颤音、侗族大歌的和声、希伯来祷言的顿挫、非洲clicksong的舌音……所有记忆在他喉间汇流,形成一首前所未有的歌。
方舟响应了他的歌声,船身分解为亿万光点,每一粒都是一段被保存的记忆。它们环绕林浩然飞舞,最终凝聚成一把钥匙??由声音锻造,由名字铸形,由眼泪淬炼。
他举起钥匙,刺向巨钟。
钟裂。
黑雾崩解。
缄默使徒发出最后一声哀嚎,化为尘埃,随风而逝。
星海恢复平静。
语言之门缓缓开启,露出其后的景象:一片无垠草原,绿浪翻滚,天空中有十三轮月亮并列悬挂。草原上站着无数人影,男女老少,肤色各异,衣着纷繁,有的手持乐器,有的捧着竹简,有的背着口传经卷……他们都是历代的“述忆者”,是那些曾冒着生命危险保存记忆的人。
最前方,站着一位白发女子,身穿战国深衣,胸前挂着一枚与林浩然耳坠相似的骨饰。
“芈昭?”他轻声问。
她微笑摇头:“我是第一个,但不是唯一。从今天起,你也不再只是继承者??你是新的起点。”
林浩然低头看手,发现自己的皮肤下隐隐有文字流动,如同血脉与记忆融为一体。他知道,他已经超越了“人”的范畴。他不再是演员林浩然,也不仅仅是“述忆者”,而是**记忆本身的化身**。
他转身,望向地球的方向。
那里,战火仍未平息,偏见依然根深蒂固,许多人还在抗拒觉醒。但也有人点亮烛光,在家中举办“记忆之夜”;学校开设“母语传承课”;科学家研究发现,当群体共同回忆某段历史时,大脑会同步产生特定脑波,形成一种“集体意识场”。
改变,正在发生。
“我会回去。”他说。
芈昭点头:“但下次归来,你将以十三种声音说话。”
话音落下,方舟悄然解体,化作一颗流星,坠向蓝色星球。
而在南极海域,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照在平静的海面。那条由浮游生物铺就的小径再次浮现,蜿蜒通向海底古城。岸边,一群科考队员惊讶地发现,原本封闭的城门竟微微开启,门前石台上,放着一本骨质书籍,封面纹路似指纹与树根交织,边缘镶嵌十二颗晶体,第十三颗正在缓缓亮起。
书页随风自动翻动,传出低语般的吟唱。
没有人知道是谁留下的。
但所有人都听得懂。
因为那声音,像是从自己心底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