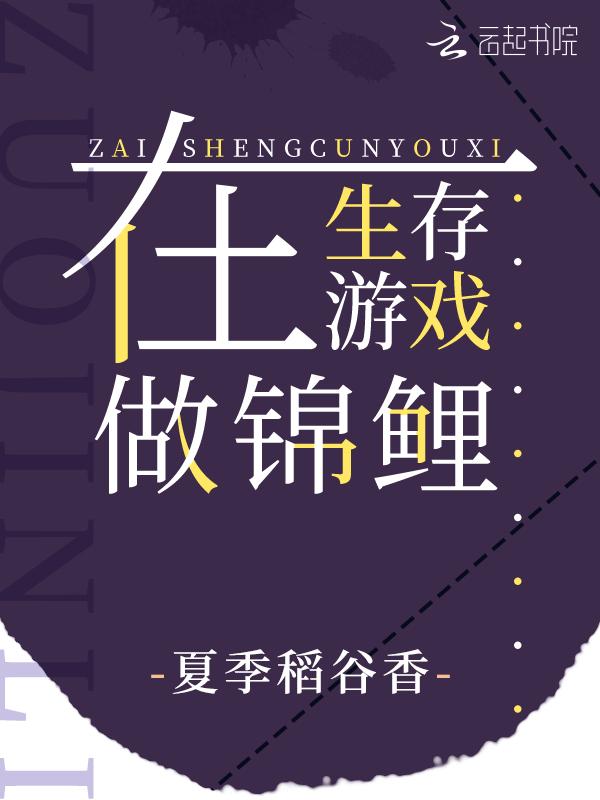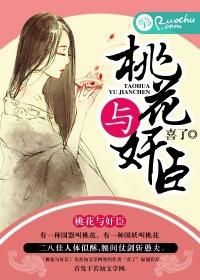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一心退休的我却成了帝国上将 > 第三百一十二章 隐秘的身份安娜的计划(第1页)
第三百一十二章 隐秘的身份安娜的计划(第1页)
看着次级负责人一脸纠结的表情,安娜顿时明白,自己临时想到的这个说法,成功让对方在撤离一事上产生了动摇。
但她也清楚,只是这样的话,根本不足以让对方下定决心。
毕竟,在魔王的眼皮子底下展开暗。。。
雪儿那一声“哥哥”像是一道裂痕,撕开了我们短暂的安宁。她的小手指向北方天空时,我心中骤然一紧??那颗正在暗去的星,并非寻常星辰,而是“守门七宿”中的天枢位,象征着命运之轴的起点。它若熄灭,意味着整个封印体系将失去锚点,黯星之门的锁链会随之松动一分。
林晚立刻命人取出《星轨图鉴》,对照实时天象。老陈颤抖着手翻到“逆命篇”,上面赫然记载:“天枢隐,地脉泣;双魂离,万灵劫。此为‘断钥之兆’,预示钥匙虽分,却已残缺。”
“不可能!”林晚猛地合上书,“心狱阵明明成功了!你怎么可能已经……”她顿住,目光死死盯住我。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如果“他”已被封入心狱,为何星轨仍在逆行?除非??封印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生效,或者,“他”根本不需要完全自由,就能影响外界。
我低头看着怀中的雪儿,她紫金色的眼眸依旧望着北方,嘴唇微动,似在与谁低语。片刻后,她忽然转头看向我,声音稚嫩却清晰:“哥哥疼吗?黑影说,你要哭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
这不是通灵,这是沟通。她竟能听见“他”的声音!
我强压住内心的惊涛骇浪,轻声道:“雪儿不怕,哥哥不哭。”可话音未落,胸口忽如刀绞,一股寒意自脊椎直冲脑门。眼前景象瞬间扭曲,祠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那口深不见底的黑井。井壁上的星图逆向旋转,速度越来越快,仿佛整个宇宙都在倒流。
“你看到了吧?”那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不再是低语,而是如同雷鸣般回荡,“心狱阵困得住我的形,困不住我的意。只要她还在,我就永远能借她的眼睛看这个世界。”
“你对她做了什么?”我在意识中怒吼。
“我没做任何事。”他轻笑,“是她本就属于‘门’的那一侧。她是纯血守门人,天生能感知所有残念、所有碎片、所有被时间掩埋的真相。而你……你只是个挣扎的囚徒,妄图用凡人的情感维系一场注定崩塌的平衡。”
画面骤然破碎,我跌坐回现实,冷汗浸透衣衫。林晚正扶着我,脸上写满担忧。“你又看见他了?”她问。
我点头,却不敢说出全部实情。如果说雪儿已经成为“他”窥探外界的窗口,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在演一场他早已预知结局的戏。
当晚,我独自登上静庐最高处的观星台。夜空如墨,七宿之中,天枢已然黯淡近半,其余六星也隐隐泛出赤红之色,宛如滴血。按照古籍记载,这叫“七星泣血”,唯有在世界更替前夕才会出现。
我取出归冥剑,横于膝上。剑身冰冷,却在我掌心微微震颤,仿佛感应到了某种即将到来的风暴。
就在这时,一道白影悄然落在屋檐上。
是那只雪白信鹰。但它这次带回的不是军符,而是一片染血的布条,缠在爪间。我取下一看,心头剧震??那是玄甲禁卫的袖章,边缘绣着一个极小的符号:**∞**
无限之环。
这个符号不属于帝国任何编制,也不见于渊阁典籍。但我认得。它出现在我每一次梦见黑井的深处,刻在井底最古老的一块石碑上,代表着“循环永续”??即黯星教团终极信仰的核心:世界必须不断毁灭与重生,才能避免腐朽。
也就是说,有人还活着,而且正在重启教团。
我立刻召集林晚与老陈,将布条展示给他们。老陈看到那个符号时,整个人如遭雷击,跪倒在地,喃喃道:“不该……不该还有人记得这个……当年先祖亲手抹去了所有记录,连记忆都被星咒封锁……”
“是谁?”林晚逼问,“谁能绕过星咒?谁能操控玄甲残魂?谁又能精准预测我们的行踪,在每一个关键节点留下线索?”
没有人回答。
但我知道答案早已浮现。
皇帝。
只有他拥有帝王之血,具备打破部分星咒的能力;只有他掌握全国密探网络,能在千里之外操纵一枚军符的出现;也只有他,曾在认亲仪式上,以指尖划破手掌,将鲜血滴入雪儿眉心时,低声说过一句无人听清的话。
而现在我想起来了。
他说的是:“**终焉之钥,已启。**”
这不是保护,是启动。
他根本不是在帮我们封印黯星,而是在推动它苏醒。
我猛然起身,冲向藏经阁最底层的地室??那里存放着《守门人录》第八卷,从未对外公开的部分。据传,只有当第七卷所述之阵完成之后,第八卷才会显现真文。
地室阴冷潮湿,空气中弥漫着陈年纸张与香灰混合的气息。我在七盏油灯环绕下,点燃三柱檀香,依照祖训默念开启咒语。随着最后一字出口,原本空白的第八卷羊皮卷竟缓缓浮现出墨迹,字字猩红,如同新写:
>“双魂者,非敌非友,乃一体两面。
>心狱可囚其形,不可灭其志。
>然天地有裂隙,人心有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