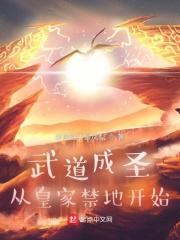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财富自由,从每日情报系统开始! > 第382章 新情报湖底价值千万的阴沉木(第3页)
第382章 新情报湖底价值千万的阴沉木(第3页)
真正的共感,始于无人回应的角落。”
宁宁读完信,走到湖边,取出一块新的情绪水晶。这一次,她刻上了陈九女儿的名字??那个从未长大、却始终活在父亲记忆里的小女孩。
她将水晶投入水中,轻声说:“今天,我梦见了一个容纳悲伤的世界。在那里,拒绝连接不再被视为冷漠,寻求帮助也不再意味着软弱。”
水面微光荡漾。
回声木沙沙作响。
**听见了。**
十年过去。
共感文明进入“后启蒙时代”。城市建起了“静默公园”,供人暂时屏蔽外界情绪;学校开设“孤独课程”,教学生如何与自我相处;每年“全球共感日”,除了点亮纪念灯,人们还会集体进行五分钟“无连接冥想”??什么都不感知,只感受自己的呼吸。
闻心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有人说他在非洲建立了首个“非共感保护区”,帮助部落保留独立意识;也有人说他潜入深海,在废弃电缆网中修复被遗忘的情感数据流。
只有宁宁知道真相。
她在一次跨国共感研讨会上收到一枚匿名包裹。里面是一本手写笔记,纸张泛黄,字迹熟悉。
翻开第一页,写着:
“记录者:闻心
时间:第3,287天
地点:赤道太平洋某孤岛”
内容全是访谈摘录。渔夫、流浪歌手、失语症患者、自闭症艺术家、战地记者、临终病人……每一个人都被问同一个问题:
“当你不被理解时,你还相信连接吗?”
答案五花八门,却有一条共同线索:他们都不使用共感设备,但他们的心声,比任何人都清晰。
最后一页,闻心写道:
“技术终将过时,制度也会腐朽,但人类渴望被听见的本质不会改变。我们建造了桥梁,但别忘了,有些人需要的是船,而不是岸。
我不寻找完美连接,我只为那些仍在黑暗中发声的人,做一盏不灭的灯。”
宁宁合上笔记本,泪水滑落。
那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
梦中,她站在一片无垠雪原上。远处,两个身影并肩而立:一个是年轻的林昭,一个是年轻的陈九。他们中间站着一个小男孩,左手牵着母亲,右手伸向远方。
风吹起他们的衣角,脚下延伸出无数条光路,通往不同方向的城市、森林、沙漠、海洋。
没有人说话。
但整个世界,都在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