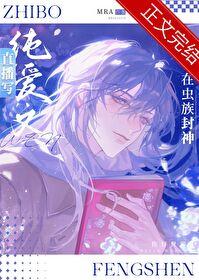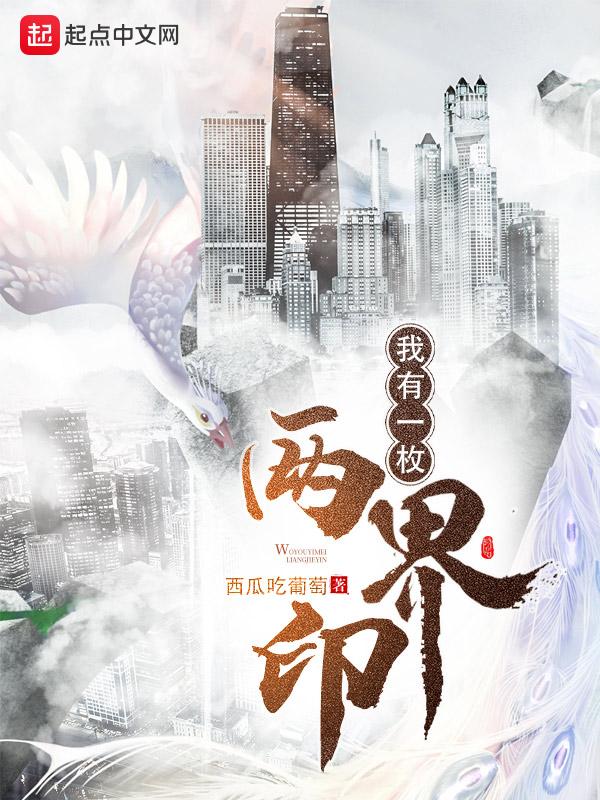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娘子,别这样! > 第616章 宋言的狠毒 灭孔灭倭六千五(第1页)
第616章 宋言的狠毒 灭孔灭倭六千五(第1页)
孔府之外。
天上还飘着雪。
那些屠城的女真和倭寇,许是将一些房子给点着了吧,火苗窜起数丈之高。赤红的火焰,照亮半边天,便是天上的雪花都折射着瑰丽的光泽,更好看了。
惨叫声,咆哮声,不。。。
海风依旧,吹动屋檐下那串铜铃,叮咚一声,轻得像是从梦里漏出来的。陈九娘坐在老位置,竹椅吱呀作响,膝上无字书温润如初,青光微漾,仿佛呼吸未止。她已不再年轻,白发盘成简单的髻,眼角皱纹深如刻刀,却掩不住眼底那抹清澈的光??那是“记得”的光。
孩子们在不远处的沙滩上排成一行,手拉着手,齐声唱着《思源谣》的新段落。这歌如今已不是一人所创,而是千人共谱。每座记忆树开花之地,便有新的歌词诞生。今日他们唱的是岭南童谣调子,夹杂着古越语的尾音:
>“我记得,南岭有碑,
>石冷如铁,字烫如血。
>我记得,守塔人盲,
>指尖划墙,声穿黄泉。”
歌声飘来时,沙地微微震颤,几行字迹缓缓浮现,如同有人以无形之笔书写。陈九娘静静看着,忽然轻声道:“是她……又来了。”
话音未落,一阵细碎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一个约莫六岁的女童跑进院子,赤着脚,手里攥着一朵半透明的蓝花,花瓣薄如蝉翼,蕊心跳动如心跳。她仰头望着陈九娘,眼睛黑得像夜里的深潭。
“奶奶,”她声音清亮,“花开了,它说你要去一趟北岸。”
陈九娘心头一震。北岸??那是当年安泰园旧址所在,如今早已沉入海底,每逢大潮退去,才隐约露出断壁残垣的轮廓。可这孩子说得笃定,仿佛亲眼见过。
“谁让你来的?”陈九娘问。
女童摇头:“不是人派我。是花自己醒的。它说……‘钟要响第九次了’。”
陈九娘猛地站起身,膝盖上的无字书滑落在地,却没有发出声响,反而在触地瞬间泛起一圈涟漪般的光晕,随即渗入泥土。她低头看去,只见地面浮现出一行静语文符号,与当年贝壳上的笔法一模一样:
>“桥将通,魂当归。执灯者,启门。”
她闭上眼,脑海中轰然响起那熟悉的钟声??第一声来自敦煌地窖,第二声来自长城烽燧,第三声来自岭南密道……直到第八声,戛然而止。还差一声。
“原来如此。”她喃喃,“最后一声,不在别处,就在这渔村之下。”
她转身进屋,取出了神龛上的陶罐。十年未曾开启,此刻指尖触到罐身,竟觉温热如活物。她轻轻揭开封泥,林素衣的日记仍在,但纸页已不再是炭笔字迹,而是整片泛着幽蓝荧光的文字,仿佛液态的记忆在流动。
她读到了一段从未见过的内容:
>“九娘,若你见此字,说明‘忆心兰’已苏醒。
>此花非我所种,乃万千亡魂共愿凝成。
>它只开一次,只为迎接‘终钟’。
>
>北岸地底,藏有静语塔残基,其核心为‘逆钟之心’??
>能逆转遗忘之力的唯一器物。
>但它需以‘记得之血’唤醒,即真正亲历过安泰园焚毁之人所流之血。
>
>你是最后一个。
>若你不赴,桥永不通。”
陈九娘的手微微颤抖。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必须回到那片废墟,用自己最后的生命之力,敲响第九声钟。
当晚,她召集全村孩童,在海边点燃油灯三百七十三盏,一如十年前那般。不同的是,这一次,每一盏灯旁都放着一片记忆树的叶子,叶上文字随风轻颤,似在低语。
沈昭没有来。但她留下了一封信,用的是最古老的静语文写就,唯有陈九娘能识:
>“我在北方种下了第七十二株记忆树,它开花了,花中浮现你的名字。
>你不必回来,若你选择留下。
>但我知道,你会走完这条路。
>因为你从来不是守护者,而是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