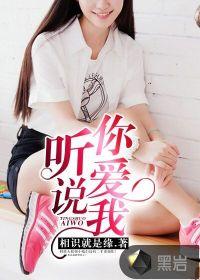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二婚嫁京圈大佬,渣前夫疯了 > 第1550章 一起去看外婆(第1页)
第1550章 一起去看外婆(第1页)
一瞬间。
饭桌上的气氛剑拔弩张。
小十从未见过这样的架势。
自家从来不会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小十抿唇,清了清嗓子,开口说道,“怎么回事?怎么还对鱼有偏见呢?人家鱼才不是七秒钟记忆,人家聪明着呢。
我骑摩托艇的时候看见了一只鲸鱼,凌派派打了招呼,等到我们转圈回来,它还冲着我们吐水,一看就是认出我们来了。”
方文溪偷偷看了看父亲的眼神后,才跟着说道,“本来就是,海豚就很聪明啊,比小孩子都聪明,怎么会有七秒。。。。。。
>**今天,我站在世界的中心说了话。明天,我想让更多人听见彼此。**
陈婉轻轻走过来,坐在她身边,没有说话,只是将一条薄毯披在她肩上。远处,守守已经睡熟,山果的房间里还亮着一盏小夜灯??那是她坚持要留的,说怕黑。
“妈妈。”小满突然用唇语比了个词,然后在纸上写,“我想办一个‘声音节’。”
陈婉微微一怔:“声音节?”
小满点头,眼睛亮得像刚落下的流星。她在纸上画了个简单的示意图:一片开阔的草地,中央搭着舞台,周围摆满了各种能“看见声音”的装置??震动地板、彩色灯光随节奏闪烁的球体、手语投影墙、还有孩子们用画笔记录“听到”的音乐的长卷。
她写道:**不是让听不见的人去听,而是让听得见的人学会用别的方式感受声音。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沟通不只靠耳朵。**
陈婉看着那些稚嫩却坚定的线条,心口猛地一热。她想起多年前那个蜷缩在福利院角落的小女孩,连哭都不敢出声。如今,她不仅开口了,还想为更多沉默的生命点亮一盏灯。
“你不怕累吗?”她轻声问。
小满摇头,在纸上画了一棵小树苗顶开石板的样子,旁边写着:**压得越重,根扎得越深。**
第二天清晨,沈知远还没起床,小满就抱着素描本敲开了他的书房门。他揉着眼睛接过本子,一页页看下去,神情从困倦变为震撼,最后竟站起身来,在原地踱了几步。
“这不只是个节日。”他低声说,“这是文化重建。”
他立刻召集团队开会。阿岩听说后激动得差点打翻咖啡:“太棒了!我们可以做一场全感官音乐会??鼓点通过地面传递震动,旋律化作光影在空中流动,歌词用手语舞者演绎,观众闭着眼也能‘听’完整场演出。”
技术组负责人提出担忧:“设备成本高,场地协调难,而且公众接受度未知。”
沈知远却笑了:“当年我们连助听器都买不起的时候,就开始教小满发音了。现在,有什么好怕的?”
会议结束时,他宣布:“‘听见春天’计划升级为‘回声行动’,第一站就是‘声音节’。预算不限,我要它成为全国乃至亚洲第一个以多元感知为核心的公共艺术节。”
筹备工作迅速展开。消息传出后,令人意外的是,最先响应的竟是一群聋校老师和听障艺术家。他们自发组建志愿者团队,有人设计触觉乐器,有人开发视觉化音符APP,还有位盲人诗人主动联系,希望朗诵一首专为“无声听众”创作的诗。
与此同时,媒体的关注再度升温。央视《人物》栏目申请跟拍全过程;《南方周末》发表专题报道《当世界开始“看”声音》,引发社会广泛讨论:“我们是否太过依赖听觉,而忽略了其他感知的力量?”
然而,风暴也悄然逼近。
某天傍晚,陈婉在整理邮箱时,发现一封来自匿名账号的邮件,标题只有两个字:**可笑**。
点开后,是一段视频链接。画面中,一名西装革履的男人站在讲台上,背景写着“中国特殊教育发展论坛”。他是国内知名心理学教授周维衡,曾公开质疑“融合教育”的可行性。
“近年来,某些打着‘爱与包容’旗号的项目正在制造虚假希望。”他在演讲中说道,“听障儿童的语言康复极限明确,强行将其推入主流教育环境,只会导致社交孤立与心理创伤。所谓的‘奇迹女孩’小满,不过是一场精心包装的表演秀。她的每一次‘发声’,背后都是巨额资源堆砌的结果,普通家庭根本无法复制。”
镜头切到一张图表,标注着“听障儿童语言恢复成功率不足7%”,下方赫然写着小满的名字,被圈红。
“更危险的是,这种个案被神化后,会让无数家长陷入盲目追逐的误区,浪费时间、金钱,甚至耽误孩子真正适合的发展路径。”周维衡语气严厉,“我们应该回归科学理性,而不是被情绪绑架。”
陈婉的手指僵在鼠标上,心跳如鼓。她下意识回头看向窗外??小满正和山果在院子里画画,笑声虽无声,却清晰可辨。
她没敢立刻告诉沈知远,也没告诉小满。可那天夜里,她辗转难眠,脑海中反复回响那句“表演秀”。
第二天,她在厨房煎蛋时失神,油锅突然起火。沈知远冲进来关火拉她出去,才发现她手腕已被烫红。
“到底怎么了?”他皱眉。
她终于崩溃,把手机递过去。
沈知远看完视频,脸色沉静如水。他没说话,径直走进书房,十分钟后,一封署名“沈知远”的公开信出现在微博热搜榜首:
>**致周维衡教授:您说得对,小满不是奇迹。她是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是两百多个日夜的发音训练,是三千多次摔倒又爬起的尝试,是我们全家倾尽所有换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