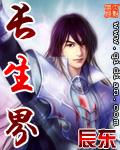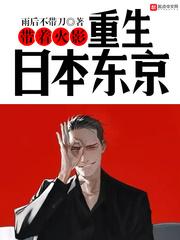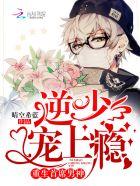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二婚嫁京圈大佬,渣前夫疯了 > 第1547章 订完婚就跑了(第2页)
第1547章 订完婚就跑了(第2页)
>你说过的爱我都存着,藏在心跳之间
>当风吹过山谷,铃铛轻响
>我知道,那是你在回答我……”
歌声未落,眼眶已湿。
三天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办的全球公益论坛在日内瓦举行。陈婉作为“听见春天”代表登台演讲。全场座无虚席,各国政要、学者、媒体齐聚一堂。
她走上讲台,没有使用翻译员,而是抬起双手,以手语开始讲述。
起初,台下有人疑惑,有人交头接耳。但随着她的动作越来越流畅,情感越来越饱满,整个大厅渐渐陷入寂静。
她说起了念安的故事,说起那个曾因失语而被世界忽视的女孩;她说起了小满,那个被遗弃在福利院角落、手腕带疤却依然愿意相信温暖的孩子;她说起了山果如何第一次写出“妈妈”两个字时泪流满面的模样。
她的每一个手势都像在雕刻灵魂。
当她打出最后一句:“我们不是需要怜悯的弱者,我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话”时,全场起立鼓掌。许多人含着泪水,跟着学习那句简单的手语:“我爱你。”
直播信号传回国内,“听见春天”微博瞬间爆红。#原来沉默也有力量#登上热搜榜首。无数网友自发录制视频,用手语说出心里从未说出口的话??给父母,给爱人,给朋友。
与此同时,国内一家主流电视台宣布将拍摄纪录片《无声之光》,全程记录听障儿童的成长历程,并邀请小满担任特别顾问。
消息传来那天,小女孩激动得整晚睡不着。她翻出素描本,一页页画下自己想象中的片场场景:有孩子们在教室里写字,有老师用手语讲故事,还有她在镜头前微笑着打出手语台词。
第二天清晨,她早早起床,穿上最干净的校服,背上画板,拉着沈知远的手要去基地礼堂练习“发言”。
一路上,春风拂面,铃铛叮咚作响。
走到半路,她忽然停下,仰头望着他,眼神清澈坚定。然后,她松开手,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一笔一划写下:
>**爸爸,我想学说话。**
沈知远心头猛地一震。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先天性重度听障、几乎从未发声的孩子来说,学说话不仅是生理挑战,更是心理上的巨大跨越。每一次发音都要依靠视觉与触觉去模仿,要忍受无数次失败与挫败。
“你确定吗?”他蹲下身,认真地看着她。
小满用力点头,眼中闪着光。她翻开本子继续写:
>**我想亲口告诉你,我有多爱你。**
那一刻,沈知远感觉心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疼得几乎无法呼吸。他紧紧抱住她,下巴抵着她的发顶,声音哽咽:“好,我们一起学。一个字一个字地练,一辈子也不嫌长。”
当天下午,他们联系了国内顶尖的语言康复专家李教授。对方听说情况后当即答应亲自指导,并组建专项小组,结合AI语音反馈系统与振动感知训练设备,为小满定制个性化课程。
第一节课在一周后开始。
治疗室里,镜子前摆着麦克风和显示屏。小满戴上骨导耳机,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声波图,紧张地攥着沈知远的手。
“来,试试看,发‘啊??’的音。”李教授温和地说。
她张开嘴,喉咙用力,却只挤出一声沙哑的气息。
再来一次。
第三次。
第五次……
直到第十次,一声极其微弱、近乎气音的“啊”终于从她唇间逸出。屏幕上,声波曲线微微起伏,像春天的第一道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