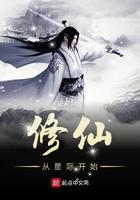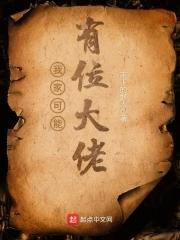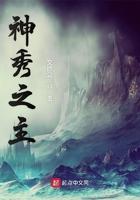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乌龙山修行笔记 > 第五百五十六章 种生道来了(第1页)
第五百五十六章 种生道来了(第1页)
想要原路返回,却谈何容易?
种生道按照之前测算的方式演算时序偏差,需要一个最初的起始方位,但这个起始方位,他找不准了。
任何人在墓道和地下暗河中折腾了几十天,重见天日后都不可能找得准。
。。。
韩念站在赎忆塔顶层,玉骨笔横于掌心,蓝花花瓣随风飘入袖口,在皮肤上留下一丝微凉的触感。他闭目凝神,体内那股源自血脉深处的记忆洪流正缓缓苏醒??不是被动承受,而是主动召唤。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自己已不再是单纯的“继承者”,而成了《人间录》真正的执笔者。
笔尖轻颤,一道银光自腕间升起,如星河倒悬,缠绕指节。这不是法力,也不是神通,而是一种更为古老的契约之力:当一个人真正“记得”时,天地便会为他降下书写之权。韩念睁开眼,眸中映出整片夜空,那由亿万记忆光点构成的人世长河正在流转不息,每一颗星辰都是一段被唤醒的故事。
他抬手,玉骨笔凌空划过。
第一个字落下,是“人”。
这一字并非写在纸上,而是刻入风中、渗入地脉、融入空气中浮动的尘埃。刹那间,乌龙山百里之内,所有正在做梦的人都在同一瞬看见了这个字??它悬浮于梦境中央,清晰得如同亲见。有人因此惊醒,有人泪流满面,更有人喃喃重复:“人……我是个人……我曾活过。”
沈清梧立于塔下石阶,仰头望着那道青蓝色的笔迹划破苍穹,心中震动难言。她曾以为《烬忆集》只是遗书,如今才明白,它是钥匙,是火种,是韩知雪留给未来的引路明灯。而韩念所写的每一个字,都在激活这把钥匙的最后一环。
阿舟悄然现身身旁,盲眼虽不能视物,却能“听”到文字在虚空中的震颤。“他在重写规则。”他说,“不是复述过去,是在定义‘铭记’本身。”
的确如此。
韩念继续挥笔:
>“人有魂,不在骨肉,而在其所记所念。
>忘者失魂,记之则归。
>故凡被遗忘者,非死也,乃困于幽冥之隙;
>凡被传诵者,非生也,乃存于众心之间。”
每写一句,赎忆塔便共鸣一次,九万三千六百碑文逐一亮起,仿佛亿万生灵齐声应和。那些早已湮灭在历史夹缝中的名字开始浮现??有的来自战乱年代无声消逝的无名兵卒,有的是饥荒年间饿死在路边却无人收尸的老妪,还有更多是在政治风暴中被抹去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影像短暂出现在村口老树下、祠堂门槛边、废弃校舍的黑板前,向亲人点头,向世人低语:“我还在这里。”
南方渔村的那个铁箱再度震动,贝叶经残卷自动翻页,浮现出与韩念空中所写字迹完全一致的内容。渔夫跪伏于地,浑身颤抖:“这不是人写的……这是天意。”
与此同时,极北冰原上的少女握紧玉骨笔,忽然开口吟诵,声音清越如钟鸣。她并不识字,却一字不差地背出了韩念刚刚写下的篇章。随着她的诵读,方圆十里冻土解封,蓝花破冰而出,连绵成海。一头濒死的雪狼挣扎起身,眼中竟泛起人性般的泪光,低声呜咽后,朝着北方深深三叩首??那里,埋葬着它幼年时被人猎杀的母亲。
西北荒漠的考古学徒们惊恐发现,那块刻着童谣的石碑正在自行补全内容。原本空白处浮现出后续诗句:
>“笔落惊风雨,墨洒动山河。
>一念通古今,万魂共此歌。
>若问先生何处去?
>千家灯火说其名。”
最后一个字成型之际,整片遗址地面龟裂,一座半埋的青铜鼎缓缓升起,鼎内盛满蓝花,花蕊中藏着一枚与韩念手中几乎相同的玉骨笔头。最年长的学徒颤抖着伸手触碰,瞬间脑海中涌入一段画面:千年前,一位史官在焚书烈焰中将竹简投入鼎中,口中高呼:“纵使天下皆忘,吾笔不死!”
“他是最早的承忆者……”年轻人泣不成声,“我们找错了方向。我们不该挖坟掘墓,该去听老人说话,该记录街头巷尾的传说……”
话音未落,远处沙丘之上,一朵蓝花迎风绽放。
韩念不知这些事,但他感应到了某种变化??《人间录》的精神网络正在扩张,不再局限于九州大地,而是像根须般穿透国界、跨越语言、刺入人类集体潜意识的底层。他已经不是唯一能听见记忆回响的人。世界各地,开始出现新的“共振点”。
巴黎一家图书馆深夜无人,管理员巡查时却发现阅览室灯光全开,桌椅排列成奇异阵型,中央一本古籍自动翻页,上面用中文写着:“你记得吗?”次日调取监控,画面显示整整三小时,空气中不断浮现出汉字,宛如有人凭空书写。馆长查阅资料后骇然发现,二战期间曾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在此自焚抗议纳粹暴行,尸体旁留有一本未完成的手稿,题为《被烧毁的日记》。
纽约地铁站,一名流浪歌手抱着吉他哼唱一首陌生民谣,歌词讲述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某位华工在修建铁路时坠崖身亡的经过。奇怪的是,这首歌从未出版,旋律也无人教过他,可当他唱完最后一句,站台墙壁突然渗出蓝色液体,凝结成一行小字:“谢谢你说出我的名字。”
伦敦大学历史系教授收到一封匿名邮件,附件是一段录音,背景嘈杂,似有许多人在同时说话。起初以为是恶作剧,但当他戴上耳机仔细分辨,赫然听清了数百种不同方言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关于一个穿灰袍的男人,在各地收集口述历史,最终消失在风雪之中。教授猛然想起,自己祖母临终前也曾提过类似人物,当时只当是老人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