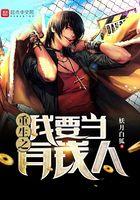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八零女翻译官被糙汉醋王宠翻了 > 316第316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第2页)
316第316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第2页)
女主持人话音一转:“但您却毅然选择回到了相对偏远的家乡,从修建第一条乡村公路起步。”语气里带上满满的探寻:“我能问问吗?您当年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的?”
主持人话音刚落,镜头便轻轻一转,平稳地对准了另一侧沙发上坐着的男人。约莫五十出头,穿一件款式简单的深蓝色衬衫,领口纽扣扣得整齐,没有一丝褶皱;鼻梁上架着副细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神温和明亮,言谈举止间透着从容与随和。
随着镜头聚焦,他面孔下方随即弹出一行白色介绍字幕:「嘉宾:杨晓风,国家级卓越工程师」。
看清字幕的一瞬间,孟呦呦僵在了椅子上,忘记了眨眼睛。
电视里,对话还在继续:“其实没什么复杂的想法。”
说着,两鬓微白的男人,目光飘向演播室远处,像是陷入了某种回忆,顿了两秒后,才缓缓开口道:“小的时候家里穷,受了不少乡亲的恩惠和托举,才考上的大学。到了毕业真要找工作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小时候自己去学校上学还得一路翻山越岭,村民们把农产品运到镇子上去卖大多靠的是肩挑背扛,很是不容易。”
他收回目光,看向主持人,“自己正好是学工程的,回去修修路挺好,能让更多的人可以方便地走出大山也挺好。”
主持人听得沉浸,频频点头,眼里满是感动,适时接过话头,顺着话题往下展开:“原来这份选择背后藏着这么深厚的乡土情结!”
她低头看了眼手里的提纲,又抬眼看向坐在对面杨先生:“您在家乡这一扎就是近十年,不仅主导修通了番州市第一条跨境通道,还陆续推动家乡建成13条交通主干线、5座便民大桥,还有数不尽的乡村小路。
这些道路桥梁,不只方便了村民和居民出行,往大了说,更是带动了边贸、旅游和本地农产品外运,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但之后您又选择前往首都,投身更顶尖的国家重大交通研究课题,这个转变背后又有怎样的一个考量?”主持人问。
杨晓风先生闻言笑了笑,语气依旧平和:“在基层待的那些年,我积累了不少交通建设的实操经验,也遇到过很多技术瓶颈。
当时就琢磨着,能不能尝试着把这些基层经验用到一些国家层面的技术研究当中,去攻克更尖端的难题,再把这些高新技术运用到更多城市的道路建设和发展中,去发挥更大的用处。”
主持人听了之后,总结道:“从番州大山里的穷小子,到清华工程学博士,再到修通家乡第一条跨境通道的杨工,而现在是牵头国家高铁冻土技术攻关的专家,您的经历听起来实在是太传奇了!”
“这一步步走来,能看得出您对自己的发展路径,每一程规划都十分明确。”主持人往前倾了倾身,目光里满是期待,“我很想请问一下,在您个人的成长道路上,有没有什么人,在做人做事的准则上深深地影响了您呢,让您始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杨晓风先生沉吟了几秒,稍微调整了一下坐姿,然后答道:“我想应该有两位。”
“哦?有两位。”主持人即时接话:“能都跟我们聊一聊吗?”
“当然。”杨晓风先生颔首轻笑。“一位是我的父亲,他曾经是一名军人,后来受伤退役回到了村子,那时候村头村尾但凡有哪家出了事,像是张家的牛丢了,李家的房顶漏了,周家两个儿子闹分家,都习惯找他来解决,他也都乐意去搭把手。
是他教会我男子汉要守护好一方水土。”
主持人全程微笑着倾听,配合着对方的叙述适时点头,做出反应。
“另一位,也是一名军人。”杨晓风先生的声音慢了些,像是在打捞久远的记忆,“那一年他们部队来我们村子助民,帮着修水渠,整田地。刚好那段时间我奶奶在山上采菌子不小心摔断了腿,我慌得不行,住院要好多钱,上学也要好多钱,而且只要我继续上学,奶奶就还得去山上采菌子。”
“所以那时候我能想到的办法就只有放弃上学,替我奶奶上山捡菌子。”讲到这里,杨先生搭在膝盖上的双手无意识蹭了蹭西装裤的布料,似有些局促,又似有些对自己年幼时的稚嫩无知感到好笑。
“但是那时候有一个军人叔叔非常严肃地教导我,叫我不要轻易放弃念书。
我就问他,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呢?
他告诉我,是为了长大以后能够拥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爱的人,让她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永远依靠上山捡菌子来维持生计。”
杨晓风先生语速轻缓,吐字清晰:“他还说,如果能力再大一点的话,那就去保护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听到这里,孟呦呦突然感觉到后脊背一阵猛烈的战栗,刺麻刺麻的一片,小店里烧红的铁煎板正滋滋冒着声响,她觉得那滚泡的油点子溅了她一身。
男人的声音持续从电视机里传出来:“我当时问他,‘就像你们现在这样吗?’
他摸了摸我的头,用一种鼓励的眼神看着我,认真回答道:‘对!就像我们一样!’
他们部队离开村子的前一晚,那个叔叔又找到我,最后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想跟我们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