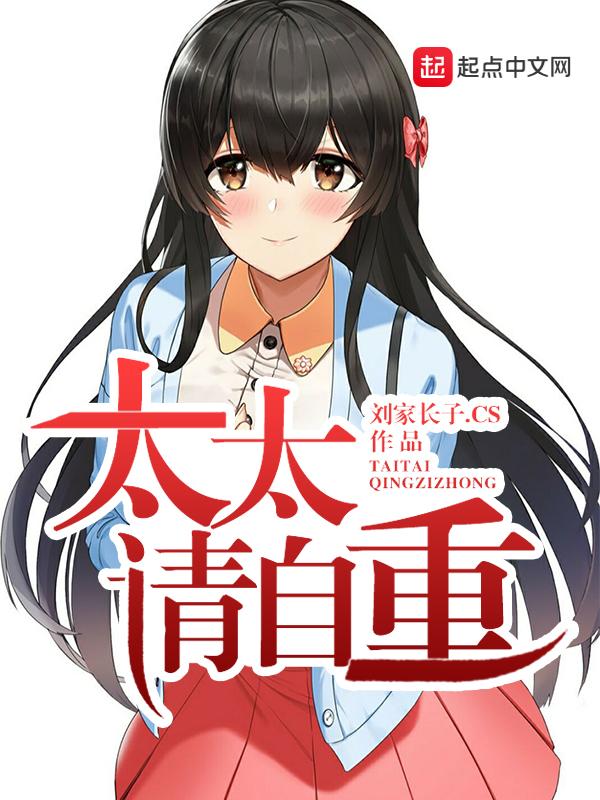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边军悍卒 > 第1082章 段家护院(第2页)
第1082章 段家护院(第2页)
>“该你写了。”
***
云南山村,梨树下的木屋依旧安静。林秀兰坐在桌前,面前摊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她的手有些抖,墨水洇开了几处,但她仍一笔一划写着:
>“今天是第十年。
>钟声园多了那一声回响,我知道,他们在等新的人接笔。
>我的身体越来越轻,像随时会散进风里。
>可灵魂却比三十年前更清醒。
>昨夜我又梦到昆仑山巅,那块石碑裂开了一道缝,里面藏着一本没有封面的书。
>我伸手去拿,书页自动翻动,全是空白。
>直到我写下第一个字,其余页面才逐一浮现文字??
>全是别人写的。
>来自不同年代,不同语言,不同笔迹。
>但他们都在说同一件事:
>‘我不愿活在一个没有真话的世界。’
>原来,执念可以接力。
>原来,死亡不是终点,沉默才是。”
写到这里,她停下笔,望向窗外。远处山坡上,一群孩子正围着一棵新栽的小梨树嬉闹。那是村里新建学校的开学礼,每个孩子都带来了一支笔,放进树下的陶罐里,作为“第一课”的献礼。
其中有个八岁男孩格外安静。他蹲在地上,用树枝在泥土上反复描画一个符号??七芒星。旁边老师问他画的是什么,他摇头不说,只低声念了一句诗:
>“宁折者,不可弯。”
林秀兰瞳孔微缩。这句诗从未公开出版,只存在于边军内部口传心法的终章。她猛地站起身,冲出门外,却见那孩子已经转身跑开,背影消失在山路拐角。
她怔立良久,忽然笑了。
手腕上的钢笔再次发烫,这一次,不是渗出血痕,而是笔帽自动旋开,露出内藏的一枚微型存储芯片。她取下芯片,放入信封,写上“致下一代执笔者”,然后放进木箱最底层,压在那套旧军装之下。
当晚,一场细雨悄然降临。雨水顺着屋檐滴落,敲打着窗棂,节奏竟与当年昆仑铜鼓的集结令完全一致。
***
三年后,东海某座无人岛礁。
一艘破旧渔船靠岸,船头站着个戴斗笠的男人,肩扛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箱。他踩着湿滑的礁石走上岸,直奔岛屿中央一座坍塌的雷达站遗址。
他是周正的儿子,名叫周明远。母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是一本烧焦一半的日记。他在十七岁那年读完最后一页,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也知道了那支银色钢笔的意义。
多年来,他走遍中国海岸线,寻找第七代边军遗留的信号塔残骸。终于,在三天前,他的接收器捕捉到一段加密频率,解码后只有四个字:
>**“此处可写。”**
此刻,他打开铁箱,取出一台老式打字机??那是周正生前最爱用的型号,型号铭牌早已磨平,唯有侧面刻着一行小字:“为真实发声”。
他将打字机摆在废墟中央的石台上,铺上一张白纸。海风吹动纸页,发出沙沙声响。
他深吸一口气,敲下第一个字母。
A。
接着是第二个。
N。